股權激勵原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股權激勵原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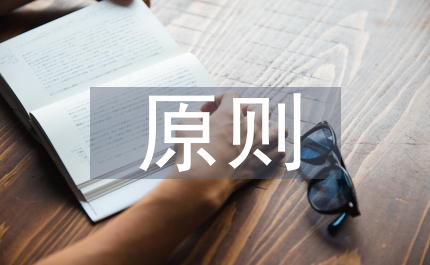
股權激勵原則范文第1篇
內容提要: 正視封閉公司股東所面臨的不同于公眾公司的現實,美國公司法律實踐日益信賴股東合理期待,常常以小股東權益為中心來界定壓制行為,創設和發展了以股東合理期待為基礎的股東權益救濟制度,并逐漸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合理期待認定標準,盡可能地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股東提供廣泛的救濟,以有效地保護受侵害股東的權益。基于合理期待落空而對股東權益進行救濟的美國公司法理念與法律實踐值得我們借鑒以完善我國股東權益救濟制度。
為了更好地保護我國中小股東權益,基于合理期待而救濟股東權益,使其免遭大股東壓制侵害的美國公司法理念與法律實踐值得我們借鑒。
一、合理期待原則的產生與發展
合理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s)是指公司股東間相互負有的以真誠、公平、符合理性的方式營運公司的義務以及股東間、股東與公司間最初具有和后來建立起來的良好企盼和愿望。美國聯邦與各州的司法實踐及制定法日益正視封閉公司股東所面臨的不同于公眾公司的現實,在公司法律實踐中逐漸產生和發展了合理期待原則,以救濟封閉公司股東權益,并為制定法所接受和認可。
(一)合理期待原則形成的法律環境
1.封閉公司的異質性與傳統公司法規則的不適宜性
封閉公司不同于公眾公司,為數不多的股東之間往往有著親密的關系,家庭關系或者其他私人關系等特殊關系和商業關系相交織。[1]封閉公司中一般不存在提供資本的人與管理企業的人之間職能相分離的情形,這種公司是公司參與者的貨幣資本投資工具,也是參與者通過被公司雇傭而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工具。因此,封閉公司股東通常希望自己既是公司股份的所有者又是公司的雇員,股東成為公司股份的所有者和公司的雇員是其參與公司的一種期待。
但是,在傳統法律規則層面上,不管是公眾公司還是封閉公司,均是按照多數決原則和集中控制原則進行運作的,持有多數表決權股份者有權選舉整個董事會或大多數董事會成員,公司權力集中在選舉出來的董事會和高級管理人員手中,因此,擁有多數表決權的股東或股東聯合事實上控制著整個公司。對于強調資合的公眾公司與強調人合的封閉公司,集中控制和多數決原則機制對兩者意義是不相同的。就公眾公司而言,這種機制促進了公司的適應性,為其提供了調和不同利益的機制,但它并不能反映封閉公司的特殊需求,封閉公司常以某種緊密關系為基礎,這使得集中控制和多數決原則很容易成為擠壓股東的工具,如終止雇傭關系,剝奪股東的投資回報權等。
公司實體永存性和股份自由轉讓性等公司規范同樣反映的是公眾公司需求,并不完全適合于封閉公司。公司實體與公司股東相分離是公司所有權獨立于公司控制的大型公眾公司的特征,公司獨立于其有壽命限制的股東,而可能永續存在。封閉公司的永續存在讓股東的困境變得更加復雜,與多數股東關系破裂的小股東面臨著多數股東無期限地使用其投資給企業的一切資本,但這些資本卻無法盡快得到回報。股份可以自由轉讓的規定及其相關規范對封閉公司而言也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公司規模和人數決定了公司股份不可能存在一個現成交易市場。沒有現成的交易市場,股份交易價格發現就具有不確定性,其交易成本會大大增加;在公司不能分配利潤時,股東也不可能利用二級市場創造“自制利潤”。[2]
司法對公司管理層決定公司方針政策和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從事公司事務權力給予尊重的商業判斷規則也主要是基于公眾公司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在封閉公司中同樣存在不適合性,如對于股東在公司中是否享有被雇傭這種期待,紐約上訴法院基于商業判斷規則,在Ingle案中對封閉公司股東是否有權不遭受公司任意雇傭權解雇問題持保守狹隘態度,但一些法律評論人士認為:“即使多數股東正當地終止小股東雇傭,在小股東不是雇員的情況下多數股東通過雇傭來繼續分配公司盈利的做法無疑是一種壓制行為,司法不應簡單地適用商業判斷規則對公司的看起來合法、正當的管理行為予以尊重。”[3](P362)
2.壓制行為制定法界定的模糊性與合理期待原則的可彌補性
很多制定法將壓制及其類似行為作為強制解散公司的制定法根據和理由,但制定法中的“壓制”或其他類似用語卻是寬泛、模糊的,事先無法準確地界定其具體內涵和外延,只有按個案實際予以確定。在封閉公司異質環境下,只有明確強制解散公司制定法的立法目的或制定法提供替代救濟的目的在于給小股東更好的保護,壓制行為和其他類似制定法用語才能更好地予以解釋。正如一紐約法院在Applicationof Topper案所說的:“壓制行為這一制定法概念只有通過審視封閉公司特質和創設強制解散公司制定法的立法目的才能最好地理解。”(注:In Application of Topper,107 Misc.2d 25(Sup 1980).)壓制行為研究的權威學者O’Neal教授和其他評論者一致認為,需充分考慮封閉公司的特質,結合個案特殊情況,以小股東合理期待為中心來界定壓制行為:(1)公司參與者通常期待著積極參與公司管理和經營企業;(2)當股東間發生分歧時,作為公司法基石的多數決原則可能為公司控制者利用來挫敗小股東公司參與者的期待;(3)封閉公司股份缺乏流通市場意味著小股東沒有令人滿意的退出方法。[4](P873-875)在Matter of Kemp&Beatley案,一持股份35%、為公司雇傭了35年的小股東指控公司其他參與者嚴重挫敗其將資本投入到封閉公司時所抱有的合期期待。法院認為:“小股東期待其在公司的所有權會使其有權得到一份工作、分享公司收益、參與公司管理或獲得其他形式的保障,這些期待是合理的,公司其他參與者盡力挫敗這些期待,小股東卻無法有效地拯救其投資;考慮到封閉公司性質和制定法救濟目的,利用原告股東合理期待作為判斷和衡量訴稱的公司其他參與者行為構成壓制是合適的。”(注:Matter of Kemp&Beatley,Inc.,64 N.Y.2d 63,484(1984).)法院因此認定本案所指控的行為應是真正意義上的壓制行為。
(二)合理期待原則的法律實踐
基于封閉公司的異質性,不少州制定法將壓制及其類似行為作為強制解散公司的根據和理由,由于州制定法“壓制”及其類似行為界定的寬泛性和模糊性,司法實踐中不斷引入合理期待原則、以小股東權益為中心來界定壓制行為,進而予以受侵害股東司法強制解散公司的救濟。不少州法院將挫敗股東合理期待視為界定壓制行為的最佳指引,北卡羅萊納最高法院常使用合理期待原則來界定制定法中所規定的股東權利和利益,專門確立了股東合理期待標準以判斷是否應該給予制定法救濟。在Meiselman案,北卡羅萊納最高法院改判下級法院裁決時明確表達了這一司法理念:“初審法院以公司控制者可能有的極端行為為關注中心,使用‘壓制’、‘行為過頭’、‘嚴重濫用’、‘不公平地謀利’等表述,其適用的法律標準是嚴重錯誤的,正確的關注焦點應該是原告股東的權利和利益,考慮公司參與者關系中發展起來的股東的合理期待。”(注:Meiselman v.Meiselman,309 N.C.279,307 S.E.2d 551(1983).)南卡萊茵州一上訴法院曾將合理期待作為界定壓制行為五大方法之一,后來州最高法院改采個案分析方法,將合理期待作為壓制行為一大指引性指標(注:Kirikides v.Atlas Food Systems&Services,Inc.,343 S.C.587,541 S.E.2d 257(2001).),將包括合理期待因素在內的眾多因素作為可以單獨認定壓制行為的指引性指標。[5](P285)華盛頓州法院的做法是:首先要求原告證明壓制行為,然后將證明責任轉移至多數股東被告,由多數股東被告證明其行為是善意的,決策是合理商業判斷的結果(注:Scott v.Trans-System,Inc.,148 Wash.2d 701,64 P.3d 1(2003).)。很多聯邦法院明確表示,對“壓制”術語應給予自由解釋,如在McCallum案,法院用這一理念撤銷了一不利于原告的即決判決動議。在本案中,公司小股東總裁與多數股東家族保持著長期交往關系,公司總裁為公司成功起了關鍵作用,當其與該家族的關系變壞時,家族股東解除了小股東總裁職務,并要低價收回為誘使其加入公司而發行給原告的股份,原告訴稱公司為報復其專業能力強而從事對其不利的行為,聯邦法院認為終止原告公司總裁職務、意圖低價收購其在公司的持份足以支持法院的買斷命令,法院適用明尼蘇達州制定法“不公平損害”要求推翻了初審法院對公司總裁不利的即決判決(注:McCallum v.Rosen’s Diversified,Inc.,153 F 3d 701(8thCir.1998).)。
隨著合理期待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廣泛運用,很多州制定法開始明確地以股東合理期待為基礎給予強制解散公司救濟或其它替代救濟,這種理念現已被幾個州制定法直接采納,密歇根州制定法將壓制行為界定為包括嚴重影響股東作為股東的利益的持續性行為、重大行為或一系列行為,但不包括股東協議、公司章程細則或反復適用的公司政策或程式所允許的行為。一上訴法院在適用這一新制定法規定時認為,“其他州已經開始適用以股東合理期待為基礎的客觀檢驗法則,這比制定法規定更具有合理性”(注:Estes v.Idea Engineering&Fabrication,Inc.,250 Mich.App.270,649 N.W.2d 84,92(2002).)。目前,有大約1/3的州在公司法中將股東合理期待作為根據或基礎授予壓制制定法救濟,如明尼蘇達州制定法要求在確定是否給予解散公司、股份買斷和其他衡平救濟時,法院應考慮封閉公司股東間相互負有的以真誠、公平和合符理性方式營運公司的義務以及股東間、股東與公司間最初具有和后來建立起來的企盼和愿望。北卡羅萊納州制定法授權法院在合理地認為為保護原告股東權利和利益所必需時采取司法行動清算公司。
合理期待原則的司法實踐和制定法的引入反映了股東權益救濟考量從以企業控制者極端行為為中心向以原告股東地位為中心的轉移,即使不能證明公司控制者有極端行為,股東仍能獲得相應的保護與救濟。不少法院認為一些制定法采用“不公平損害”(Unfair Prejudice)用語就意味著解散公司救濟的焦點不僅僅在控制股東的過錯上,“股東在企業創立初期具有對企業運行的合理期待,如果這種合理期待實現的前景遙遙無期,解散公司或強制買斷其在企業的利益或許是封閉公司環境下利益的流動性與穩定性間明智的妥協”。[6](P1)這種嚴重后果勢必會使多數股東在實施壓制行為時考慮到方便、低成本的救濟會使其實施的剝削行為負上沉重的代價,同時,也促使多數股東以贏得小股東支持的方式從事公司行為。
二、合理期待原則的適用范圍與過錯要求
合理期待原則源于以股東合理期待是否落空作為判定是否予以救濟的普通法法律實踐,主要運用于司法強制解散公司或予以替代救濟時的訴因基礎的司法認定上。受普通法的影響,一些制定法也開始接受、認可合理期待原則,并與司法實踐一道協同發展了合理期待原則制度,形成了日益完善的合理期待原則適用規則。
(一)合理期待原則的應然適用與排除適用
在合理期待原則的產生與發展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合理期待原則適用更多地是針對封閉公司,因為合理期待原則的適用是依附于以壓制行為為根據的強制解散公司制定法規定的。盡管許多將壓制行為規定為強制解散公司根據的制定法均開放地適用于一切公司的股東,但司法適用這一救濟時幾乎都只限于封閉公司。[7]近來制定或修改的制定法還將基于壓制行為而救濟限定在其界定的封閉公司范圍之內,進而將合理期待原則的適用也限制在其界定的封閉公司范圍之內,如紐約州壓制制定法僅適用于股份不能公開交易的公司,新澤西州壓制制定法僅限于25名股東以內的公司。采用《法定封閉公司示范法補充規定》(Model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upple-ment)的州將壓制制定法限定在只適用于按照要求修改公司章程或置入特別選擇條款成為法定封閉公司50名股東以內的公司。因此,合理期待原則的適用對象大多限于封閉公司,很少適用于公眾公司。事實上,正是封閉公司股東所面臨的風險激勵著現代立法和司法給予特別的救濟。[8](P6-27)
遵循《法定封閉公司示范法補充規定》的制定法會對以壓制行為為基礎尋求解散公司救濟的封閉公司股東構成實質性影響。盡管超過制定法規定股東人數的公司不大可能存有制定法規范所架構的期待關系那樣的密切聯系,但如果公司有兩、三個積極參與者和大量的被動參與者,一個被終止雇傭的主動參與者也可能存有使其落空的期待,此時相關制定法卻不具有適用性;《法定封閉公司示范法補充規定》的門檻標準也帶來了極大影響,如兩人公司或三人公司沒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選擇成為法定封閉公司,他們就不能得到壓制行為制定法救濟。實際上,只有極少部分公司按照制定法要求選擇成為制定法所涵蓋的法定封閉公司,有的是因為忽視沒有選擇,有的是對新法律制度由于缺乏既定先例支持持不信任態度。要求封閉公司選擇特殊身份更適合于那些賦予封閉公司更大靈活性以變通集中控制和多數決原則等傳統制定法規范的特別立法規定,大多數要求進行這種選擇的州制定法基本上是授權性的。大約20多個州有適用于法定封閉公司的特別制定法,其中有一半以上州要求股東進行這種選擇,這些要求進行選擇的特別制定法關注焦點在允許封閉公司變通公司治理結構,只有佐治亞州規定以壓制行為或類似根據尋求強制解散公司救濟只適用于選擇法定封閉身份的公司。壓制行為制定法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為了給予公司參與者更大空間架構其相互關系,有的是為了對不可能事先做出安排的事宜提供一個法定的解決沖突的方法,因此,意在保護不能有效參與公司事務和獲得回報的封閉公司小股東制定法就不應該以是否選擇為條件,要求進行選擇無疑是假定小股東可以事先預料到可能降臨的災難為前提的。[9](P1-15)為此,明尼蘇達州法院在Berreman案中認定,普通法對封閉公司的界定仍繼續適用于判定信義義務關系之目的,無論封閉公司的制定法定義和具體制定法救濟是如何規定的(注:Berreman v.West Pub.Co.,615 N.W.2d 362,374(Minn.Ct.App.2000).)。由此可見,盡管一些制定法限制了基于壓制行為而救濟的適用范圍,進而縮小了合理期待原則的適用范圍,但司法實踐中往往規避制定法的限制性規定,擴大適用于一切封閉公司。[10]
隨著合理期待原則適用范圍、對象的擴大和司法適用的日益增多,股東不能證明公司控制者極端行為時往往仍能獲得相應的保護與救濟,加之合理期待原則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制定法對其界定的滯后性,如何防止原告股東濫用合理期待訴因基礎以保護公司利益和多數股東的正當、一貫行為成為法律實踐倍加關注之所在,并逐漸發展出合理期待原則排除適用的理念和情形,以使公司多數股東和公司不會遭受沉重的打擊或者說是毀滅性的后果。“關注原告”的司法理念要求法院判斷確定原告不正當行為是否可以作為不給予救濟的基礎。北卡羅萊納州法院在解釋適用Meiselman案標準時要求股東合理期待落空與其過錯行為之間要有一定的因果聯系時才可以不適用合理期待原則。當小股東自身行為令人反感,法院往往沒有必要關注小股東權益,不為其提供救濟。在Miehaud案中,法院認為,“多數股東解雇持份25%小股東總經理職務不違反信義義務,因為公司正以令人驚訝的速度虧損;鑒于公司糟糕的表現,小股東就雇傭的正當期待單獨不足以證明多數股東行為構成壓制”(注:Miehaud v.Morris,603 So.2d 886(Ala.1992).);法院有時以“不潔之手”來認定小股東的不當作為。一紐約法院在Mardikos案中拒絕了原告解散公司的要求,因為原告兒子在原告認可下組建了一與父親想解散的公司形成競爭的公司,法院認為,“盡管原告沒有嚴重不當行為存在,但允許其子組建與公司構成競爭的新公司,說明‘不潔之手’存在”(注:Mardikos v.Arger,116 Misc.2d 1028,457 N.Y.S.2d 371(Sup 1982).)。
當然,即使小股東存有過錯時,法院也往往不會輕易否決提供救濟的可能。在Royals案中,原告訴稱自己的性騷擾行為導致公司中斷了自己的應得補償,終止了其在公司的管理職務,禁止其進入公司內。法院認為:“盡管原告行為的確應該受到相應懲罰,但這種懲罰不應該影響其獲得公平回報,原告的補償與實在的服務沒有聯系,僅是一種退休基金安排以換取公司低于市價買斷其持份而已。”(注:Royals v.Piedmont Elec.Repair Co.,137 N.C.App.700,529 S.E.2d 515(2000).)當多數股東提出因為小股東的自身行為導致了多數股東的行為時,如訴稱其是因為沒有銷售業績、工作表現沒有效率等被解雇,或終止雇傭致使其期待落空,法院仍會給予一些救濟,但如果工作表現令人不滿意是因為小股東極端的不當行為造成的,法院一般不予以同情。
(二)過錯要求的理論論爭與實踐
在合理期待原則適用上是否要求存在過錯行為為前提,曾經存有很大的爭論。John Hetherington和Michael Dooley教授曾認為廢除過錯原則是救濟封閉公司潛在剝削所必需的,因此建議制定法要求多數股東應小股東請求無條件收購小股東在公司的利益。[11](P48)按照他們的建議,勢必會廢止法院按壓制行為制定法履行的“守門人”職責,取而代之的是一方便的低成本的救濟,使多數股東壓制行為代價沉重,促使多數股東以贏得小股東支持和信任的方式為公司行為。有反對者認為賦予小股東強制性權利會導致債權人不愿意為封閉公司提供信用,小股東會利用強制買斷權強化自己的經濟利益而損害其他投資者利益,使社會失去對企業的信任。這些反對意見還涉及到司法解散救濟本身。他們認為:“法院不應代表小股東輕易地從制定法中推導出從企業撤資的權利,這樣的權利會妨礙多數股東經營企業的機會行為,甚至會扼殺一切投資機會,法院應權衡公司僵局倍增所帶來的交易成本以及股權資本和債務資本價格上漲所帶來的不利。”[12](P290)在反對輕易解散公司時,Robert Hillman教授認為:“應給予封閉公司穩定性和永續性更大程度的尊重,解散公司的標準應考慮多數股東被迫重構公司資本時稀缺資金成本和輕易解散公司對全體債權人和信用提供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注:轉引自Bradley,An Analysis of the Model Close Corporation Actand A Proposed Legislative Strategy,10 J Corp Law,1985,(840).)
盡管如此,受普通法合理期待原則影響,有些州已在其制定法中明確規定了強制解散公司救濟的無過錯根據,放棄了解散公司救濟與過錯必然相聯系的觀念,如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亞及北卡羅萊納州制定法明確授權法院為保護原告股東權利和利益需要而準許強制解散公司救濟申請;路易斯安拉州制定法授權法院在公司目標完全落空或不得不全部放棄或者目標的實現完成變得不切合實際時解散公司。還有的州允許法院在股東分歧嚴重以至影響公司營業和事務并危及全體股東利益時解散公司。[13](P6-35)
三、合理期待的司法認定
合理期待是一個極具靈活性的概念,需要司法實踐中根據個案具體認定,如認定因雇傭關系而產生的合理期待需考慮參與者間各種關系和交易全貌予以審查和評估,尤其應考慮因任何原因終止雇傭的買斷協議的存在和雇員沒有資本投入而是作為補償計劃一部分獲得少量股份的事實。[13](P517)美國司法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判斷某種期待是否為合理期待的參考標準:
(一)合理期待的外觀性與外在性
在封閉公司中,各方所有的商業條件不可能全部擬定在公司章程、細則或單獨簽訂的公司成立契約和股東協議中,其協議條件經常是口頭的,甚至是存在于模糊或半模糊的共識之中;即使公司參與者將他們的交易條件設置在書面的股東協議之中,他們對公司營業的參與也常常是以書面協議中沒有提及的前提和假定為基礎的。[14](P886)股東間的期待必須從各方行為中而不僅從書面文件中提取,因此,法院允許從正式的書面協議之外去建立期待,無需以書面文件證明合理期待,但小股東負有證明這些期待存在的義務(注:Jaffe Commercial Finance Co.v.Harris,119 Ill.App.3d 136,74 Ill.Dec.(1st Dist.1983).)。
股東單純的主觀意愿不能構成合理期待,主觀希望和愿望落空不能觸發制定法救濟,合理期待中的期待必須為其他各方所知曉的。北卡萊茵州最高法院在Meiselman案中認定,原告的期待要具有合理性,這些期待必須為其他股東所知,或為其他股東所認可,或是他們共同期待的,不為其他參與者知曉的私人持有的期待不是合理的期待(注:Meiselman v.Meiselman,309 N.C.279,307 S.E.2d 551(1983).)。在Longwell案,持份50%股東訴稱其多次要求變換公司總部的地點、改變公司管理結構、解雇公司的律師和會計師,并試圖說服公司其他董事支持其要求但都沒成功,因此對公司管理層徹底失望,請求法院解散公司。法院認為:“根據公司的一貫做法,這些行為不構成壓制。”(注:Longwell v.Custom Benefit Programs Midwest,Inc.,2001 SD60,627 N.W.2d 396,400(S.D.2001).)一阿肯色州判例進一步表明主觀愿望不能構成合理期待。在Taylor案,共計持份49%的兩股東訴稱其期待參與營業管理。法院認為:“另一方清楚地表明了只有持份51%以上能控制公司者才能參與公司管理,持份49%的股東當著公司特許權許可方同意不參與公司管理,表明原告對平等地參與公司管理不存在合理期待。”(注:Taylor v.Hinkle,360 Ark.121,200 S.W.3d 387(2004).)
(二)合理期待的重要性與動態性
合理期待必須是對投資者參與企業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期待。從主觀上講,具有重要意義的期待對于不同公司的不同股東可能存在著差異,但從客觀上講,只有多數股東行為嚴重挫敗小股東決定加入企業時所抱有的至關重要并且就一般人來說在同一環境下都可能具有的某種期待,才能被視為能適用合理期待原則的壓制行為。在Matter of Kemp&Beatley案中,法院注意到申請人的期待是一個被動投資者的普通性期待,因此,拒絕了持有1/3股份的股東強制解散公司的要求。如果參與者的期待是每一股東都能主動地參與企業,那么拒絕繼續雇傭某一股東或不按比例分享企業投資回報可以被視為該期待是如此重要并足以支持解散公司救濟。在Matter of Wiedy’sFurniture Clearance Center案中,原告股東懷著積極參與的合理期待回到家庭營生之中,其后該股東因家族不和而非其他合理原因被擠出企業,法院因此予以公司解散救濟(注:Matter of Wiedy’s Furniture Clearance Center Co.,108 A.D.2d 81,487 N.Y.S.2d 901(3d Dep’t 1985).)。在McCallum案中,法院認為:“終止原告股東CEO職務并低價贖回為誘使其加入公司、繼續接受公司雇傭而發行的股份行為違背了原告股東以CEO身份繼續雇傭的合理期待。”在Clark案中,法院認為:“繼續雇傭和有意義地參與企業管理可以是小股東的合理期待,在具體案件中決定其是否是合理期待是一個事實問題,不能由即判決動議來解決。”(注:Clark v.B.H.Holland Co.,Inc.852 F.Supp.1268,1274(E.D.N.C.1994).)與此相對照,俄勒岡州最高法院在Baker案中認定:“阻止一49%持份股東檢查公司記錄、不通知其參加公司會議不是足以支持公司解散或授予其他衡平救濟的嚴重行為,正如紐約州上訴法院在Matterof Kemp&Beatlay所說的,‘單單是對公司或其他股東失望不必然等于壓制,但是沒有達到合理正當的期待顯然是壓制行為。’”(注:Baker v.Commercial Body Builders,Inc.,264 Or.614,507P.2d 387,56 A.L.R.3d 341(1973).)
合理期待不限于最初具有的期待,參與者間的期待可能隨著企業發展而變化,法院在判斷是否存有期待時應考察參與者間關系的歷史發展。在封閉公司中,最主要的交易條件往往是在企業的初始階段形成的。因此,法院應重點關注初始關系,參與者間最初的共識特別有助于評估多數股東日后的行為,初始協議可能才是雙方真實的交易談判條件,這正是英國法院認為1948《英國公司法》第210條中壓制行為只能根據個案具體情況以小股東合理期待為中心才能進行最好解釋的原因。[14](P38)但這些期待會發生變化,需要法院考慮特定交易或控制者行為有關的所有因素。不少法院認為紐約法院在Matter of Kemp&Beatley案件只關注申請人決定加入企業時期待的做法過于狹隘,還應考慮案件其他特定事實。司法和立法均寬泛地理解合理期待,不僅看企業成立當初業已存在的股東間的期待,還關注隨后在公司交易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期待,這使合理期待原則不僅適用于各方在經營中發展起來的新期待,還可適用于通過贈與或繼承而成為公司股東的這些參與者的期待。在Matter ofSchlachter案(注:Matter of Schlachter,154 A.D.2d 685,546 N.Y.S.2d 891(2d Dep’t 1989).)和Matter of Smith案(注:Matter of Smith,154 A.D.2d 537,546 N.Y.S.2d 382(2dDep’t 1989).),法院分別將合理期待原則適用于通過贈與或繼承而獲得的股份。
四、合理期待原則對我國的啟示
從基于合理期待落空而救濟股東權益的美國公司法理念與法律實踐中獲取一些有益的東西,有助于審視和完善我國股東權益救濟制度,有助于實現對切實受到侵害的股東予以有力保護的法律訴求和我國公司法規范的現代化。
(一)我國股東權益救濟制度審視
縱觀我國公司法律制度,現行《公司法》將公司分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權益救濟方式有不區分兩者性質和區分兩者性質的不同救濟。[15](P185)不區分公司性質的救濟主要包括《公司法》第22條規定的撤銷之訴、第34條規定的股東知情權制度和第150條規定的代位訴訟;區分公司性質的救濟主要包括《公司法》第75條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股權買回請求權和第106條規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的累計投票制。
1.不區分公司性質的救濟
(1)撤銷之訴。《公司法》第22條規定,公司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無效。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60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股東依照前款規定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應公司的請求,要求股東提供相應擔保。
(2)股東知情權制度。《公司法》第34條規定,股東有權查閱、復制公司章程、股東會會議記錄、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和財務會計報告。股東可以要求查閱公司會計賬簿。股東要求查閱公司會計賬簿的,應當向公司提出書面請求,說明目的。
(3)代位訴訟。《公司法》第150條規定,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152條規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有本法第150條規定的情形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連續180日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書面請求監事會或者不設監事會的有限責任公司的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監事有本法第150條規定的情形的,前述股東可以書面請求董事會或者不設董事會的有限責任公司的執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監事會、不設監事會的有限責任公司的監事,或者董事會、執行董事收到前款規定的股東書面請求后拒絕提起訴訟,或者自收到請求之日起30日內未提起訴訟,或者情況緊急、不立即提起訴訟將會使公司利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前款規定的股東有權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2.區分公司性質的救濟
(1)針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股權買回請求權。《公司法》第75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對股東會該項決議投反對票的股東可以請求公司按照合理的價格收購其股權:(一)公司連續五年不向股東分配利潤,而公司該五年連續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規定的分配利潤條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轉讓主要財產的;(三)公司章程規定的營業期限屆滿或者章程規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現,股東會會議通過決議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續的。
(2)針對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的累計投票制。《公司法》第106條規定,股東大會選舉董事、監事,可以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或者股東大會的決議,實行累積投票制。本法所稱累積投票制,是指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或者監事時,每一股份擁有與應選董事或者監事人數相同的表決權,股東擁有的表決權可以集中使用。
3.現行救濟制度的不足
從現行制度規定可見,我國現行《公司法》對于股東權益的救濟制度甚少,利用起來也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限制。[16]撤銷之訴中,股東必須提供相應的擔保;查閱公司會議記錄、賬簿等時,股東應提交書面申請說明目的,在公司(也就是有控制權的股東)有合理根據認為股東查閱會計賬簿有不正當目的,可能損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絕提供查閱;在代位訴訟中,股東必須經過一系列前置程序才能進行訴訟,而且訴訟利益歸于公司,這必然會打壓股東在公司遭受損害時進行訴訟的信心;有限公司股東行使股權買回權被圈定在有限的范圍內;[17](P173)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在遭遇擁有絕大多數股份的股東時,累計投票制也無濟于事。更為主要的是,在現有制度中,并不存在救濟壓制侵害致使股東合理期待落空的途徑,盡管《公司法》第183條規定了司法解散公司制度,但該制度的適用有嚴格的限制性條件,并非針對大股東壓制侵害中小股東、致使其合理期待落空的情形。
(二)我國股東權益救濟制度的借鑒
1.引入合理期待原則的必要性
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者將資本投入公司有利于資本的集合和責任的分擔,但我國公司法只規定了信息查詢制度、累計投票制度等較少的事前救濟制度來保護持份較少的投資人在公司中的弱勢地位,大股東利用自身在公司的控制地位通過形式合法的程序排除小股東的表決權、回報取得權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時,我國公司法的救濟制度顯得蒼白無力。我國公司法所規定的代位訴訟、撤銷之訴等事后救濟制度發揮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代位訴訟本質是通過保護公司利益減損的方式間接保護股東在公司的利益;撤銷之訴首先在行使上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且需要提供擔保和經歷漫長的法院訴訟,即使法院撤銷了股東會、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可能也是遲來的正義。因此,我國有必要借鑒美國公司法中的合理期待原則來完善股東遭受壓制、合理期望落空時的權益救濟制度。
2.對合理期待原則的具體借鑒
對合理期待原則,我國公司法律制度可以從如下六大方面予以借鑒:
第一,對合理期待原則制度予以明確引入。通過對現行公司法的修訂,在我國公司法律制度中引入美國的以壓制及其類似行為為根據而強制解散公司的制度,并以中小股東權益為中心,適用合理期待原則來界定壓制行為。具體而言,可在《公司法》第183條中增加如下條款:“當股東在公司運營中受到排擠、壓制或在公司的利益受到侵害,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的,公司股東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人民法院應以中小股東權益為中心、關注股東合理期待認定壓制擠出行為。”
第二,對合理期待的內涵予以明確厘定。通過公司法司法解釋明確規定:“股東的合理期待是指公司股東間相互負有的以真誠、公平、合符常理的方式營運公司的義務以及股東間、股東與公司間最初具有和后來建立起來的良好企盼和愿望。合理期待的司法認定應考慮如下因素:(一)期待必須是對投資者參與企業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期待;(二)期待必須為其他股東所知悉的期待;(三)期待不限于公司成立時股東間業已建立的期待,包括在公司運營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期待;(四)期待不限于通過股東間的章程、協議、其他書面文件可以證明的期待,包括存在于書面文件之外的期待。”
第三,對合理期待原則的適用范圍予以明確界定。通過公司法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合理期待原則適用對象為非上市公司。”我國公司法將有限責任公司視為人合性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資合性公司,而沒有像美國公司法那樣將非上市公司視為人合性公司、上市公司為資合性公司。將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人合性公司對待,這是提供救濟的關鍵之處。就合理期待原則而言,適用對象為非上市公司具有合理性,因為這些公司不存在股份能夠自由交易的二級市場。
第四,對原告股東的無過錯要求予以明確限制。通過公司法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在原告股東合理期待落空而予以救濟時,原告股東即使存有過錯也不影響法院以此為基礎而給予相應的救濟措施,除非原告股東行為明顯不當,且其合理期待落空與其過錯行為之間存有明顯的因果聯系。”在中小股東合理期待落空、希望解散公司的案件中,案件審理的相關目標是‘期待’而不是‘過錯行為’。強制解散公司或替代救濟是為了戒除中小股東對其持份缺乏流動性的擔心,否則會不必要地強化多數股東控制之手,將中小股東鎖定在缺乏流動性又不能為其帶來所期待利益的投資之中。
第五,變通合理期待原則適用后果。通過公司法司法解釋明確規定:“解散公司的法律后果只適用于大股東嚴重侵害致使中小股東合理期待徹底落空、公司無法繼續經營的情形。其他需要救濟的,法院可酌情予以替代救濟。”我國立法及司法傾向于謹慎適用解散公司這種極端的法律救濟手段,一般不會因為大股東行使形式合法的程序對中小股東造成不利影響而輕易做出解散公司的裁判。因此,在尊重我國司法傳統的基礎上,建立強制解散公司的替代救濟機制,引入美國司法實踐中的股份強制買斷制度;解散公司的法律后果只針對大股東的嚴重行為以及中小股東合理期待落空、公司無法繼續運作的情形。
第六,明確合理期待證明責任。通過公司法司法解釋明確規定:“請求強制解散公司或尋求替代救濟的中小股東原告負有證明合理期待存在和合理期待落空的責任。”這樣規定符合普通民事權益救濟中“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也可以避免中小股東濫用合理期待原則不當尋求司法救濟、累訴大股東,以平衡保護大股東管理、經營公司的合法權益。
注釋:
[1]趙學剛.求解有限責任公司股東預期利益實現的制度困境[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93-96.
[2]胡光志,楊署東.信義義務下的美國小股東保護制度及其借鑒[J].法律科學,2008,(6):98-104.
[3]Moll.Shareholder Oppression and“Fair Value”:of Discounts,Dates,and Dastardly Deeds in the Close Corporation[J].54Duke L.J.,2004.
[4]O’Neal.Close Corporations:Existing Legislation and Recommended Reforms[J].33 Bus.Law,1978.
[5]Bahls.Resolving Shareholder Dissension:Selection of the Appropriate Equitable Remedy[J].15 J.Corp.L,1990.
[6]Hillman.The Dissatisfied Participant in the Solvent Business Venture:A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ve Permanence of Partner-ships and Close Corporations[J].67 Min.L.Rev.,1982.
[7]趙萬一,吳曉峰.美國法的排擠式公司合并及對我國的借鑒意義[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7):44-50.
[8]F.Hodge O’Neal&Robert B.Thompson.O’s Neal and Thomson’s Oppress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LLC Member[M].Thomson/West,2007.
[9]O’Neal&Thompson.O’Neal and Thompson’s Close Corporation and LLC:Law and Practice[M].Thomson/West,2005.
[10]周涵婷.論合理期待理論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的實踐運用[J].上海金融,2011,(3):97-101.
[11]Hetherington&Dooley.Illiquidity and Exploitation:A Proposed Statutory Solution to the Remaining Close Corporation Problem[J].63Va.L.Rew.,1977.
[12]Easterbrook&Fischel.Close Corporations and Agency Costs[J].38Stan.L.Rev.,1985.
[13]Moll.Shareholder Oppression v.Employment at Will in the Close Corporation:The Investment Model Solution[J].1999 U.Ill L.Rev.,1999.
[14]樊云慧.英國少數股東權訴訟救濟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15]曹富國.少數股東保護與公司治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16]陳璞,馮昭玖.論股東知情權救濟制度的完善[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6):134-137.
股權激勵原則范文第2篇
十年前,某中型企業通過全員持股的方式,完成了從政府部門下屬的國有企業向股份制企業的改造和轉變。十年間,企業在起起落落中成長,目前基本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但是,圍繞股權激勵而產生的諸多問題也隨之而來。
最初企業改制時,由于經營狀況很差,員工能力和水平有限,在政府“甩包袱式”的改制思路下,企業采取了全員持股的方式。企業成立十年間大量人員退休,截止到2013年,退休人員所持股份接近總股份的50%;在這個階段,一批骨干也成長起來,但由于當初股份制改造時,這些骨干還只是企業的一般人員,職位較低,所持股份極少;而近年來新進員工則根本沒有股份。這樣,似乎造成了一個局面——在職員工在給退休員工“打工”,打消了企業內部很多員工,尤其是骨干員工的積極性。
盡管企業通過各種手段從一些老員工手中回購了一小部分股權,并且準備對一批骨干員工實施股權激勵,這時卻又遭遇了一個新尷尬:很多骨干員工不愿意自掏腰包認購股權,而是希望獲得更多的業績獎金。很顯然,員工看到的僅僅是股權的分紅功能,只是將股權激勵看作工資的一個補充而已。
設計“以未來為導向”的股權激勵
很顯然,上文提到的問題根源在于企業在最初股份制改造時根本沒有進行系統的股權激勵設計。應當承認,企業在當初改制時需要通過“全員持股”的方式完成全民所有制員工的身份“贖買”,并使改制方案合法化。在這種思維導向下,激勵對象就自然地被鎖定在當時的在職員工范圍內,也沒有考慮到企業未來發展中必然產生的新的激勵需求,而這種鎖定很顯然是與股權激勵的導向相偏離,也為今天出現的各種問題埋下了伏筆。
事實上,任何激勵都是以未來為導向,激勵的著眼點和目的在于激發員工的未來業績,是“向前看”的;即使是“向后看”的認可員工過去貢獻的獎勵、績效工資,其著眼點仍然是提升員工的未來績效,作為激勵高級形式的股權激勵更是如此。股權激勵的特殊之處在于用企業未來的錢來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可以說,員工從股權激勵中所獲得的任何收益都是員
工自身努力的結果。如果能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那么企業就可以明確股權激勵的對象,即那些在企業發展戰略中處于關鍵地位、發揮核心作用的員工。
正是由于股權激勵以戰略實現為根本目標,因此股權授予應當是有條件和業績目標要求的。比如,股票期權只有在企業股價超過行權價時才有意義,這實際上是為期權授予對象設定了一個終極的企業發展目標。對于大量非上市公司來說,其股權激勵也是需要設定目標的,而且目標可以更加多樣化,并將員工實際所得的股權額度與相應的目標考核掛鉤。
股份是否有價值,用更通俗的話說,即是否“值錢”,其核心仍然是企業戰略能否實現其價值。股權的價值絕對不僅僅在于分紅,更多的是伴隨企業發展而來的股權溢價。因此,合理的目標設定不是為股權獲得設定難度,而是讓員工感覺到企業股權是有極高價值的,并能代表企業對自己的高度認可。這就要求企業在股權激勵之前,進行明確的戰略和發展步驟規劃,即讓員工在當前就能看到所持有股份的未來價值,并與企業達成高度共識。只有這樣,股權才真的“值錢”,才會得到激勵對象的認可和珍惜。正是因為缺少這樣的戰略眼光,在很多企業多年前進行股份制改造的時候,大部分員工對股票內部認購權毫無感覺,甚至將股份低價賤賣,導致多年后在企業快速發展和上市時捶胸頓足、唏噓不已。
改進股權激勵的策略
通過戰略梳理達到“上下同欲”
戰略梳理往往容易被企業忽略。股權固然是將激勵對象與企業聯結為共同體的方法,但是能否達到企業和員工共同獲利的目標,則取決于股權的價值,股權的價值又取決于企業的發展程度。如果企業在股權激勵之前沒有規劃出一個明晰的戰略目標和發展路徑,股權是不會具備價值含量的。
同時,員工對企業戰略是否認同也是評價激勵對象是否值得激勵的一個關鍵評價要素。試想,如果作為激勵對象的企業骨干不認同企業戰略,或者所謂的骨干員工無法在企業戰略中找到明確的定位和作用,那么股權激勵能有多少效用呢?
總之,股權激勵的目的是將企業和骨干員工聯結為一個共同體,股權激勵只是一個黏合劑,而這個聯結活動的核心必然是具有長遠眼光的企業戰略規劃。
從戰略角度確認激勵對象和激勵額度
理順戰略和股權激勵之間的關系后,激勵對象和激勵額度的確認就變得更加明晰。股權激勵的大體對象必然是那些能夠在企業戰略中起到關鍵作用的骨干員工。從具體激勵對象的確定上,要通過企業戰略分析來明確那些處于戰略節點上的關鍵員工,并在確定股權激勵總體額度的前提和讓員工獲得與其在戰略實現中發揮作用相匹配的股權額度的基本原則下,通過各種方法確定每個激勵對象具體的激勵額度,具體方法包括對偶比較法或更加注重量化的海氏評估法等。
建立多層次的股權激勵體系
股權激勵存在多種方式,需要針對不同類別員工的需求層次采用差異化方式。
股權激勵方法有不同的分類原則,按照以注重當期現金回報,還是以持續的股權溢價為角度進行分類,可以將多種股權激勵方式大體分為在職股權激勵和注冊股權激勵兩種。
在職股權激勵是一種“淺層次”的股權激勵方式。如果公司尚未建立起獨特的盈利模式和可持續發展路徑,員工則會非常注重當期現金收益,那么公司采用偏重現金分配的在職股權激勵方式較為適宜。在職股與崗位相關聯,意味著員工在職即享受股份分紅權而沒有投票權、繼承權等,離職則自動取消股權。
注冊股激勵則是比在職股激勵更為高級的激勵形式。一般來說,上市公司都會按照相關制度實行規范的股票期權模式;對于非上市公司來說,一方面無法像上市公司那樣具有明確的市場股價,另一方面,非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方案可以更加靈活。這里簡要介紹一種與股票期權相仿的適合于非上市公司的期股模式。
首先,確定股權激勵的開始時點,激勵人員和激勵額度基數,并確定股權的注冊時點,在開始時點和注冊時點之間的時間段,如3年,即構成對各激勵對象的考核區間。
其次,按照企業戰略,針對不同激勵對象設定考核指標和績效標準,同時將考核結果與激勵額度掛鉤,并確定實際激勵額度。明確激勵對象獲得股權的方式,即股權如何定價,是否需要支付資金購買,采用怎樣的定價方式購買等。
再次,可以在完成注冊后規定股權的鎖定期,如3-5年,即在該期間內股份權利受限,企業應對該期間
內表決權利以及離職做出特殊規定,其目的在于為骨干人員戴上一副“金手銬”。
最后,企業可以根據發展的節奏,按照上述辦法不斷推出多期股權激勵方案;而股權來源可以是與企業發展相匹配的股份增發,這樣也可以解決股份來源的問題。
規范股權激勵操作
由于股權激勵涉及股份注冊、股東權利義務、公司章程以及治理結構等諸多法律問題,因此在操作方面需要較高的規范性。為了避免類似文章開頭案例中的企業在改制中忽視退出機制,結果造成“在職的給退休的打工”現象的出現,企業在股權激勵中,要從股權獲得、業績考核、注冊以及保密、退出機制上做出清晰完備的規定,并簽訂相應的法律文本,從而避免企業與員工之間的糾紛。同時,這些規范要與《公司法》以及《企業章程》保持一致,應通過合法的程序產生效力,并聘請法律專業人士或機構對此進行審核和鑒定。
解決骨干成長與新員工進入股權問題
企業可以通過完善股權退出機制、增資擴股等方式,解決骨干員工成長與新員工進入后的股權授予額度的來源問題。
股權激勵對象在離職、退休及喪失勞動能力、死亡等情況下,都應當將股份退回。對于在職股來說,由于并沒有進行工商注冊,且一般在授予時已明確規定員工離開現崗位即失效,因此較易處理;對于已經完成工商注冊的注冊股來說,則需要企業以一定的價格進行回購,一般采取根據企業估值的一定比例定價的方式回購,還需約定回購股份的處置方式以及代持機制,如約定現股東有權購買該股份、在股東之間分配,或者以股權池的形式留作后續股權激勵使用等。
增發也是解決股權激勵來源的主要方式。當然,增發不是在企業現有規模的基礎上濫發股票、稀釋老股東股份的數字游戲,而應當與企業發展切實地結合起來,每次增發都應當有企業規模、資產和利潤的支撐,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老股東的股份比例因受到稀釋而不斷縮小,但實際上的財富絕對值卻在不斷增長。只有在這個前提下,老股東才愿意支持股權激勵。這也是企業“舍得”的智慧。
逐步完善股權統籌布局
由于股權結構關系到企業的實際控制權,中小企業股權激勵中需要考慮到股權統籌布局問題。誰是企業的真正主人,誰真正關心企業的長期發展,都是關系到企業健康發展的關鍵問題。
股權激勵原則范文第3篇
如今,股權激勵越來越受到重視,普及率日增。截至去年10月底,滬深兩市已有775家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涉及股權激勵計劃1077個,其中229家推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股權激勵計劃。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2月,克明面業、江南嘉捷、永新股份等眾多上市公司了注銷部分股權激勵股票的公告――激勵對象離職,公司注銷其未解鎖的股票,這是和平處理。也有涉及重大糾紛、訴諸法律的處理方式,其中王茁與上海家化2014年的股權激勵官司至今未見塵埃落定的公開信息。
從公司的角度出發,股權激勵是為了提高員工歸屬感和認同感,增進工作效率,提高公司收益,因此一旦離職就不應當繼續享有股權激勵,應注銷、轉讓給其他股東或支付給公司違約金。而從員工的角度看,股權應當由自己處分。公司到底該如何合法、合理地處理好人走了股權激勵怎么辦這一問題?
激勵糾紛不斷
近年來,員工離職后的股權激勵糾紛不少。
上海家化董事會認為,王茁對公司內控管理上存在重大缺陷負有責任,解除其總經理職務,王茁尚未解鎖的股權激勵股票2014年6月被回購并注銷,數量為315,000股,每股價格10.94元,回購總價款3,446,100元。回購價是彼時市價的三折。這筆錢數額不小。王茁稱,“我并不是不看重錢,我其實很看重錢。”當年,在勝訴勞動仲裁后,王茁和上海家化的股權激勵官司開打。
2015年的富安娜天價股權激勵索賠糾紛案和回天新材股權激勵糾紛案,都是因為高管離職跳槽并套現而引發的糾紛。這兩起激起業內爭議的案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由于上市公司進行股權激勵時,與員工簽訂股東協議,對股權激勵作出限制性的規定,包括在一定年限內不辭職、不發生侵占公司資產導致公司利益受損的行為,否則需將所持股份轉讓給其他股東,或者向公司支付違約金。這兩起糾紛最終以公司勝利告終,富安娜案件獲賠超過4000萬元,堪稱A股“史上最貴”的股權激勵索賠系列案,回天新材公司已依法追索了1500萬元。
此外,近年離職股東公司章程無效的案例漸多,大多因為公司股東會通過《股權管理辦法》,規定“股東因為崗位發生變化、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關系而導致其所持有的股份必須轉讓”,而離職股東持異議不愿強制轉讓。這些案件中,各地法院都持有近乎相同的態度,即公司可以對股東轉讓股權進行限制,但這種限制不能直接剝奪股東自身應享有的自益權,除非得到股東本人的同意。股權轉讓前,原股東仍應享有分紅的權利。有法院提出,“雖然規劃公司的股東均應受公司章程和《股權管理辦法》中股隨崗變規定的約束,但股東對其所有的股權仍享有議價權和股權轉讓方式的決定權。”
因此,在實施股權激勵時,需考慮如何采用合法合理的方式,對離職股東加以限制。是采取股東協議的方式,還是利用章程進行約束?值得思索。
雙重法律關系
公司可以與員工簽訂股東協議,約定股權激勵的條件、方式和離職必須轉讓股權或者支付公司違約金,這種協議實際上是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由于該強制退股行為系采取股東事先約定主動轉讓股權的方式,并不違反法律法規相關的強制性規定,應當認定其具有約束效力。從富安娜和回天新材案可以看出,法院支持股東協議可以就股權激勵對離職股東進行約定,離職了就強制股權轉讓或者支付違約金。
當然,在簽訂這種股權激勵協議時,員工往往處于談判的劣勢地位。回天新材案中股權激勵糾紛案件中,股東戴宏程表示,“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我們也沒有考慮那么多,公司要求簽字,我們就簽了”。股東許俊則表示,“我們對這樣的《協議書》有異議,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作為員工是處于弱勢的,你如果不簽,就可能拿不到股份,員工相當于沒有選擇。”
由于被激勵的對象是員工,在股權激勵后與公司之間既是勞動關系又是“股東-公司”關系,因此股東協議也具有勞動合同和民事合同的雙重性質。在富安娜股權激勵糾紛案中,就引起了法律適用爭議,究竟是勞動法的適用范圍,還是民商事法律規范的內容?該案的一審法院認為,由于被告的股權收益是依股東身份而獲得的,不是勞動報酬,違約金也是完全依據被告股東身份而做出的,應當適用民商事法律規范調整。違約金條款實際上只是股權回購條款,一旦股東辭職,就觸發收益轉讓的條件,而非一般意義上的違反義務履行的情形。
事實上,員工通過簽訂股東協議建立的股東-公司關系來源于勞動關系,且勞動關系不受股東-公司關系的影響,因此股權激勵協議雖然適用民商事法律規范調整,也不能違反勞動法的相關規定,如剝奪勞動者的自由擇業、辭職等權利。
章程限制講究
世界范圍看,各國公司法大多允許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進行限制。我國《公司法》規定“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公司的章程在初始訂立時,體現更多的是合意原則,股東全體一致同意才能通過初始章程。然而章程修改時,只需滿足三分之二的資本多數決形式:很多時候,淪為控股股東對公司股權洗牌的工具,排擠少數股東。實踐中,法院認為未經股東本人同意,利用資本多數決修改后續章程,強制股權轉讓的行為無效。這一觀點具有合理性。
因此,從公司合同的角度,需要區分初始章程和后續章程。就初始章程而言,股東合意一致設定的股權強制轉讓負擔,應當認為是一種自愿約定;而后續章程修訂中,如果設置了股權強制轉讓的負擔,也應當得到該條款約束下的全體股東的一致同意。
善用股東協議
處理好離職后股權激勵問題,公司可重點關注三個方面。
激勵計劃盡量采取股東協議的形式,與特定的被激勵員工簽訂,明確合同的性質、股權激勵適用的條件、時限,離職股東必須強制進行股權轉讓,將收益返還給公司等。
股權激勵原則范文第4篇
【關鍵詞】股權激勵 盈余管理
一、研究背景
股權激勵,作為一種對高級管理人員進行長效激勵的手段,起源于美國。據統計,到1997年年底,美國已有45%的上市公司實施了股權激勵計劃。2005年年底,我國出臺了《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并從2006年1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
股權激勵的特點主要有長期激勵、人才價值的回報機制與公司控制權激勵三點,實施的關鍵則在于激勵模式選擇、激勵對象確定、購股資金來源與考核指標設計四部分。股權激勵的模式有很多,但目前為止主要以股票期權和限制性股票為主。
自2006年1月1日起,陸續有上市公司開始實施股權激勵計劃。2007年全年有13家上市公司開始推出方案;進入2008年后受金融危機影響A股價格回調,僅第一季度就有21家上市公司推出方案;目前為止據不完全統計已有超過600家上市公司實施了或正在實施股權激勵計劃。
隨著股權激勵機制的發展與成熟,股權激勵所引發的盈余管理問題也開始出現。根據自利原則,公司高層管理者會為了滿足自身利益需求(達成業績條件、避稅或通過高價出售股票賺取收入)而進行盈余管理,這損害了股東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
二、文獻綜述
為解決上市公司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所導致的委托問題而產生的股權激勵機制能夠有效使管理層與股東的利益一致化,而出于自利原則,管理層也有動機通過盈余管理或信息披露等手段提高自身的薪酬。
Leininger W,Linhart P,R.Radner在論文中提到:自身持股使得管理層有較強動機進行會計操縱行為,并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上市公司利潤操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層持股。Jensen MC與Meckling WH在論文中闡明:僅僅持有少量股份無法使管理層有很強動機最大化股東權益,因為他們更有動機最大化自身薪酬;實證分析表明: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上市公司業績會隨之增加。Dechow P,Sloan R,Sweeney A在文章中提出,持股前提下,高管會隨著自己買入賣出股票的時機而調整報表中可操縱的項目。
在股權激勵計劃實施的過程中,高層管理者盈余管理的動機與時機也有所不同。以股票期權形式實施的股權激勵計劃中,為使行權價盡可能低,管理層會選擇隱藏利潤、推遲公布利好消息等手段壓低股價;若確定某年業績條件無法達成,則會遞延確認收入以確保第二年業績條件可以達成;在行權期出于節稅目的也會隱藏利潤、推遲公布利好消息等壓低股價,而在準備大量賣出時通過放出利好消息等將股價炒高。
Bergstresser與Philippon在研究中發現,因股權激勵計劃,管理層未來薪酬水平與股價直接相關,管理層有動機通過操縱利潤的方式影響股價,從而影響自身未來的薪酬水平。Pearl Meyer在文章“Option pricing abuse and boards”中提出,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中通常存在三種盈余管理手段,即壓緊彈簧(spring-loading)、躲避子彈(Bullet-dodging)和行權價回溯(Backdating)。壓縮彈簧是指在利好消息公布前先公開股權激勵計劃,以壓低股價;躲避子彈則是指在利空消息之后馬上公布股權激勵計劃,避免其實施后股價下跌與實施前股價過高;行權價回溯是指壓低股票期權方案股權激勵的行權價,管理層能夠立刻獲得賬面收益。
三、案例分析
本文以萬科A(000002)為例,分析上市公司在實施股權激勵方案過程中的盈余管理行為。
(一)公司簡介
萬科企業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5月,注冊資本110.1億,是目前我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企業,總部位于廣東深圳。
萬科于1988年開始進軍房地產行業,1991年成為深交所第二家上市公司,并于1993年開始確立公司核心業務為大眾性住宅。
2011年,萬科實現銷售面積共計1075萬平方米,銷售金額共1215億元;2012年銷售額超過1400億,銷售規模持續居全球同行業首位。
(二)股權激勵方案簡介
萬科A自2006年起至今共實施了兩項股權激勵計劃,分別是2006~2008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與2011~2015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詳細內容見表1:
(三)盈余管理分析
2006~2008限制性股票股權激勵方案期間,相關年報顯示:2006、2007年萬科的凈利潤分別增長59.56%和110.81%,全面攤薄凈資產收益率分別為15.39%和16.55%;EPS增長率分別為 35.81%和87.18%,超出業績考核標準很高。公司有動機隱藏部分2007年利潤遞延至2008年確認以保證業績達標。
從報表中預收賬款來看,2007年公司預收賬款增長近150%;從結轉率來看,2007年全年銷售額523.6億元,結算額351.8億元,結轉率67.1%左右,遠低于近幾年80%左右的標準。這說明公司存在遞延確認收入以平滑利潤的盈余管理。
06~08階段股權激勵計劃因股價因素與2008年經濟危機導致的業績不達標而失敗后,萬科籌劃了新一期的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并在業績考核標準中去除了股價標準。
萬科新一期股權激勵計劃在2011年4月8日獲得證監會批準,5月9日完成了股票期權的授予登記工作,行權價格定為8.89元。此后,公司借分紅派息多次下調行權價格,而萬科此前的分紅派息比例并不高,這很可能是借助分紅派息向管理層輸送利益。分紅派息詳見表2:
參考文獻
[1]Bergstrsser D &T.Philipoon“CEO Incentives and earning management.”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0)
[2]Bernstein“A.Options:middle managers will take the hit,commentary”.Business Week,2002(9):9.
[3]Daniel Bergstresser,Thomas Philippon.“CEO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0):511-529.
[4]Dechow P,Sloan R,Sweeney A.“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Accounting Review,1995.
[5]Jensen MC,Meckling WH.“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eonomies,1976,3(4):305-360.
[6]Leininger W,Linhart P & R.Radner.“Equilibria of the sealed-bid mechanism for bargaining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89.(48):63-106.
[7]Pearl Meyer.“Option pricing abuse and boards.”The Corporate Board,Sep/Oct,(2006):5-11.
[8]《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2005,12,31.
[9]《萬科A首期(2006~2008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2006.04.28.
[10]《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2011.03.
[11]《萬科A年度報告》,2006~2013.
[12]羅富碧,冉茂盛,杜家廷.《國外股權激勵與經營者信息披露研究綜述》,商業研究,2009.10.
[13]趙祥功,俞瑋.《股權激勵中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方式的比較研究》,經濟師,2011.01.
股權激勵原則范文第5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政軍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左大培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包明華
正略均策合伙人 高繼紅
和君咨詢股權激勵研究中心負責人 路 明
背景
前不久,中國北車公布了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計劃向343名公司高管、核心人員授予股票期權,2012年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總數為8603.7萬股,占公司目前股本總額(103.2億股)的0.83%。隨后,具有央企背景的中航電測也擬推股權激勵。一時間,“央企股權激勵”這個敏感舉措再次招來熱議。
目前,中國上市公司掀起股權激勵,但其中鮮有央企身影。在推行股權激勵的A股上市公司中,八成以上為民營企業,地方國資控股企業占比不到10%,央企更低于6%。而2012年上半年,截至6月7日已經有40家上市公司公布股權激勵草案,另有59家公司已將計劃付諸實施。
從2006年下發《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推進股權激勵,到2008年《關于規范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制度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規范喊停,再到2010年底在非上市國有控股企業實施分紅權激勵,國資委對央企管理人員中長期激勵措施的探索一直走走停停,謹慎前行。近期,除烽火通信、中國海誠這樣規模較小的央企股權激勵獲得通過,大型央企中國建筑去年的申請至今仍未批復。也正因此,央企的每一次嘗試皆成為業內關注的焦點,這次北車之舉亦不例外。
央企股權激勵為何不積極,謹慎背后又有著怎樣的爭議?央企股權激勵何時迎來推廣?《國企》雜志特邀業界專家一同探討這個頗具爭議的話題。
爭議不應成為“否決票”
《國企》:前不久中國北車嘗試股權激勵再次引來熱議,為什么對普通國企和民營企業來說非常普遍的股權激勵在央企卻會引發持久爭議?您對這些爭議如何看待?
張政軍:爭議是多方面的,但不能因為爭議而否定央企股權激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首先,外界對央企股權激勵的一個疑問是,不少央企處于自然壟斷或者限制進入的行業,難以判斷業績提升究竟是激勵帶來的,還是自然壟斷地位或者行業內競爭不充分帶來的。同時,一些行業的企業,有的價格受到國家管制,有的承擔較多社會責任,可能會影響企業效益,甚至導致企業虧損,實際上難以衡量企業業績與經理層努力程度和專業程度的關系,更談不上用股權來長期激勵高管。國資委應根據企業經濟屬性、功能和行業管制等具體情況作區分,比如把不同企業分成特殊目標、公共產品、戰略重要和完全競爭等類別,對前三類企業將特殊目標、公益目標等設置為觸發激勵的前提條件,然后將企業績效和薪酬相掛鉤。但對于水泥、建材、工程等完全競爭企業,應盡快推行股權激勵。
其次,公眾擔心股權激勵會讓本身已經很高的央企高管薪酬水平上再上一個臺階。這種看法不成熟。在良好監管下進行適當設計的股權激勵方案,不會也不應該成為給央企高管盲目發福利、漲薪酬的手段。應站在較高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如果能夠將企業管理層的收益和企業發展成長捆綁在一起,付出少量成本,可能帶來的是企業大的發展。
最后,外界還擔心股權激勵容易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應該說,在公司治理不完善、董事會權責沒落實、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確實有了股權也不見得能夠發揮激勵作用。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另一面,如果因為激勵不足、企業經營不善、投資風險估計不足導致虧損,不也是一種國有資產流失嗎?這些擔心完全可以在技術層面通過規范制度設計和方案設計去規避。北車這次的股權激勵草案為經營者提供的是一種期權,并不一定會提升高管薪酬,其收益完全取決于管理者對企業長期發展做出的努力,與企業發展是共贏的,不會造成國資流失。
包明華:第一,近幾年來對央企老總薪酬問題一直爭議不斷,加之股權激勵被很多人誤解為給老總的福利和薪酬,所以央企股權激勵才會引發爭議。實際上爭議的核心是沒有真正理解股權激勵的實質。股權激勵曾經在2008年被叫停,原因在于當時很多企業的激勵方式不規范,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
第二,有觀點籠統認為所有資源性央企都不能實施股權激勵,但是股權激勵的基礎不是跟其他企業比,而是同一企業同等條件下將現在和未來的經營狀況相比。就算是企業壟斷所得的收益,仍然可以比較。但是也需要考慮一些特殊的企業,比如石油類企業的營利水平主要取決于國際市場原油價格和國家的原油價格控制,最后才是企業努力。我們需要研究清楚企業業績多少是取決于經營,適合采取股權激勵的前提是企業經營業績的百分之八十是由管理者決定的。
左大培:一般批評集中在國企私有化和加大收入差距。當年國企改制、管理層MBO的時候就曾經出現國有資產流失,這樣的擔心和批評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因此就不搞股權激勵,我們只能加強制度設計。
至于壟斷央企是否能實施股權激勵,據我看,說央企壟斷就是一個偽命題,在很多行業都不成立,比如中石油、中石化是寡頭競爭,南車北車有很多國際競爭對手。這需要國資委做調研,企業的競爭性有多大,壟斷性有多高?壟斷性越高,股權激勵就應該越小。
高繼紅:壟斷性央企不適合股權激勵。第一,壟斷性國企的業績主要取決于國家壟斷性資源和政策,激勵經營者個人有失公平。第二,壟斷性國企的使命不應是逐利,而應承擔特定的社會責任。股權激勵可能會淡化責任,強化逐利性,背離了壟斷性國企存在的初衷,也會對社會造成很大危害。
在發達國家,對于壟斷性國企大多未實施股權激勵。日本多數國企分布在鐵路、郵政、電信、基礎設施等公共事業,以及金融、煙草、鹽業等壟斷行業,管理高度集權,沒有股權激勵。競爭性央企可以推股權激勵,但在股權分配比例、業績指標設置上要慎重。
《國企》:那么股權激勵究竟有何作用?對央企是否必要?
張政軍:央企施行股權激勵很有必要。首先,上市公司的股價變化能較好地反映企業績效和發展潛力,上市公司對公司經營層進行股權或期權激勵是國際通行舉措,也是最有效的激勵措施之一。央企也是企業。
其次,央企作為很多行業的排頭兵,參與國際競爭也需要股權激勵。國際競爭拼的就是配置資源、開拓市場的能力,而聚集優秀的管理人才、調動他們的長期積極性對提高競爭力至關重要。
最后,現在對國企管理者的業績考核采用企業規模、利潤、收益率等財務指標,偏重短期激勵。一個企業的經營績效往往是以前多年在制度變革、戰略規劃和調整、組織效率提高、技術創新、工藝流程改進等方面積累基礎上體現出來的。股權激勵是長期激勵,鼓勵管理層面對長期發展。
高繼紅:股權激勵最核心的作用是解決委托結構下的內部人控制問題。國有企業本質上也是企業,這一原理同樣適用。
路明:以創業板開啟為標志,大批中小成長型企業成功上市,同時行業高端人才通過所持股權的資本增值身價暴漲。對企業來講,“人才的市值時代”已經到來,“核心人才越來越貴”已成為不爭的事實。120分位的激勵水平來的就是120分位的人,60分位的激勵水平來的就是60分位的人。在這個大背景下,股權激勵已成為當今中國企業成長過程中無法回避的戰略性命題,對于國企也一樣。因此,國務院國資委2010年底在部分央企開展分紅權激勵試點,是央企循序漸進完善人才激勵體系、爭奪核心人才的重要舉措,對于全面提升央企競爭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具有重要意義。
包明華:股權激勵能夠把企業利潤最大化和管理者個人收入最大化有機結合,是最好的一種激勵方式。首先,股權激勵省成本。比如股票期權,行權時間內股價上漲的錢不是企業的稅后利潤,而是市場支付的。其次,股權激勵效果好。西方發達國家80%以上的大型跨國公司是強制性股權激勵。比如聯想的神州數碼之前的經營狀況很差,后來讓管理者持股,效益突飛猛進,柳傳志就要求在聯想控股全面推行。最后,央企都已建立了多元化股權結構,作為企業,不能禁止管理者和員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左大培:股權激勵保證企業經營者的利益和股東利益一致,促進他們謀求企業長期發展。現在有質疑國企研發工作做得不好,很大程度上在于領導的長遠意識不強,因此有長遠激勵是好事。
需激勵也需約束
《國企》:經過多年的發展,您覺得現在的央企股權激勵實踐存在哪些問題?
高繼紅:現在央企股權激勵仍在試水。第一,為了規避社會對公平性的質疑,目前限制首次激勵額度不多于總股份比例的1%,股權激勵收益不超過高管年薪的40%,激勵力度過小。第二,不應一刀切,應根據不同企業設置不同標準。第三,業績指標設置不當。目前有些企業業績指標設置過低,成了高管的造富工具;有些企業則設置過高,導致股權激勵計劃流產。
路明:2010年底國資委提出的分紅權激勵允許“所有權與分紅權分離”,是一次很好的探索和嘗試。但目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約束過度、激勵不足的問題。國資委和財政部規定,激勵對象股權激勵收益占股權激勵授予時薪酬總水平(含股權激勵收益)的最高比重原則上不超過40%,股權激勵實際收益超出上述比重的,尚未行權的股權不再行使或將行權收益上交公司。同時,也規定了嚴格的業績考核指標制定。這些規定導致國有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效果非常差,甚至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管理層推出股權激勵的意愿不強,“還不如拿業績現金提成”。近幾年很少見到有國有上市公司推出股權激勵計劃,原因也在于此。
在實際操作中,股權激勵通常的激勵邏輯是:業績考核(橫縱向對標)公司業績增長高激勵水平下的公司/股東股權投入激勵對象個人收益實現。因此,股權激勵作為長效人才激勵機制,需要激勵與約束相結合,才能保證公司的良性運轉,進而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對于國企上市公司股權激勵來講,在嚴格業績考核的同時,要有高激勵水平的保證。而激勵水平的確定需要對企業所處行業、所在區域的整體激勵水平進行系統梳理,重點進行行業內標桿企業的激勵水平比對,判斷企業在行業中的總體激勵水平,從而為確定股權激勵水平提供參考依據。
《國企》:未來如何豐富和完善央企股權激勵制度?
左大培:為規避社會質疑,需要在制度設計上多加注意。第一,制度設計合法合規,操作流程必須透明,不能暗箱操作。要對所有股東負責,尤其是上市公司,要通過網絡征集普通股民意見,再開股東大會征得股東同意。第二,只能針對已經正式采取了股份公司形式的國企。第三,股權激勵必須真正為國有資產保持增值服務,不能私有化。第四,央企要禁止經營者持大股。第五,要嚴格控制數額,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
路明:目前,由于治理機制不健全、資本市場不完善、行業不成熟、企業市場化程度不高以及國企自身還存在諸多問題,股權激勵不可能大面積鋪開。因此,國企股權激勵應本著“循序漸進、穩步推進”的原則,可先在競爭性行業和高新技術行業(比如國家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選取一批優質國企進行股權激勵改革試點,改革方向重點在激勵與約束的平衡,即將激勵對象個人收益與業績指標增長掛鉤浮動。在試點中逐步積累經驗,擴大范圍。
高繼紅:完善股權激勵制度的關鍵是完善央企治理結構,使企業的所有者能真正監督企業經營者。我們也可以借鑒國外的一些有效的做法,充分發揮監事會的作用。如德國國有企業是由股東大會選舉出監事會,其中普通職工、管理人員和國家代表有一定的比例要求,再由監事會選出董事會。董事會直接向監事會負責,也向股東大會負責,監事會對董事會直接行使監督權。而在我國,監事會在形式上與董事會并列,在實際中監事會地位低于董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