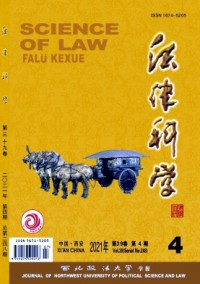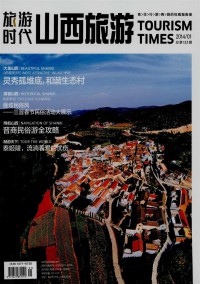對文化人類學的看法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對文化人類學的看法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對文化人類學的看法范文第1篇
【關鍵詞】人類學轉向/人種志方法/科學技術人類學/文化解釋學/本土方法論
【正文】
社會學與人類學1是兩個有著密切關系的獨立學科,在它們的發(fā)展史中,其理論與方法的互相滲透與借鑒,對這兩個學科都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就科學社會學的發(fā)展史來說,至70年代中期以來,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相伴隨,出現(xiàn)了“人類學轉向”這種現(xiàn)象〔1〕,在文獻中也出現(xiàn)了科學技術人類學這個提法。
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anthrohologicalturn),也可以稱之為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我簡稱為對科學的人類學研究。
那么,這種人類學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著什么意思?我認為,至少包含著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個含義是把現(xiàn)代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來研究。在這里,作為文化現(xiàn)象考察,并不是斯諾所提的獨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與人文文化相對立的科學文化,而是把科學當作整個人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作與宗教、藝術、語言、習俗等文化現(xiàn)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種。這樣就把現(xiàn)代科學納入了人類學的研究范圍。第二個含義是,對科學的社會研究采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選出某個科學家集本的場所,對科學家及其活動進行人種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對所觀察到的現(xiàn)象作詳細的記載、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說第一層意思是從宏觀上把現(xiàn)代科學納入人文文化范圍,決定了研究的總傾向,那么,人種志的研究就屬于微觀的經(jīng)驗研究。在我看來,知識社會學的宏觀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觀傾向發(fā)生學的研究[2]正好與這兩方面是相對應的。從這個角度說,整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都和“人類學轉向”有直接關系。
(一)
人類學轉向的含義之一:科學是詩文化系統(tǒng)之一
特拉維夫大學教授、科學史家耶胡達·埃爾卡納在《關于知識人類學的嘗試性綱領》一文中明確地提出要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系統(tǒng)來考察。他提出,在傳統(tǒng)上,“科學很少被認為像藝術或宗教那樣是屬于人文文化整體的,因為它被看作是某種不相同的、獨一無二的、互相背離的東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維度:宗教、藝術、科學、意識形態(tài)、普通常識、音樂,是相互聯(lián)系的,它們都是文化系統(tǒng)。”[3埃爾卡納從人類學角度探討這個問題,認為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系統(tǒng)來考察的觀念,可以追溯到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特·格爾茨的觀點。在他的論文《深描:邁向文化解釋學的理論》中,格爾茨說:“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質上是符號論的。和M·韋伯一樣,我們相信,人類是掛在由他自己織就了的意義之網(wǎng)上的動物。”我們必須把“文化看作那些網(wǎng),因而對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種尋求規(guī)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尋求意義的解釋性科學”。[4]我注意到,雖然格爾茨在他的論述中是把科學列入文化解釋的范圍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審慎的態(tài)度(后面還要講這一點)。而埃爾卡納同樣是把科學作為文化解釋的對象,并且根據(jù)他對格爾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對科學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釋。
而這也正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論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代表人物,馬爾凱、巴恩斯、布魯爾等人都在他們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對科學的社會研究的重點放到科學知識上面,并把自然科學知識等同于其他知識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現(xiàn)象。關于這個問題,我已在拙著《科學社會學》一書的第十章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在這里主要是把這種理論傾向與“人類學轉向”聯(lián)系起來。
愛丁堡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學知識和社會學理論》一書中就指出,科學是一種信念,只是一種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確的信念,他認為,科學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科學是亞文化的4集合’,作為一種亞文化現(xiàn)象,科學當然受到外部的整個大文化的影響。[5]因提出“強綱領”主張而著名的布魯爾也是把科學當作文化現(xiàn)象、人類學現(xiàn)象來對待的。他的“強綱領”的第一條就把科學知識與信念并列,并且認為可以歸結為社會的原因。[6]他在評述維特根斯坦的知識的社會理論時曾明確地說“數(shù)學是人類學現(xiàn)象”。[7]
馬爾凱在他的著作《科學和知識社會學》中,以專門的篇幅論述了這個問題。該書第三章的標題就是“科學中的文化解釋”,鮮明地表示出文化人類學的傾向,這也就是說,他要對科學作一種文化意義的解釋、文化意義的分析。他的這種文化意義的解釋和分析是怎樣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學社會學中關于科學家行為的社會規(guī)范的爭論,分析了默頓的規(guī)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規(guī)范,認為,在科學中,科學家的社會行為規(guī)范是多種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場合都共同遵守某種特定的規(guī)范,并不存在一種體制化的機制來保證科學家們都一致遵從或信奉某組特定的規(guī)范。在科學中,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語言公式(verbalformulation),這就為科學共同體、為科學家們提供了節(jié)目單(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科學家們可以靈活地使用它去分類不同社會背景中的不同職業(yè)行為。”因此,關于規(guī)范的討論就走到了關于科學的文化資源的說明。”[8]這也就是說,科學規(guī)范并不是像默頓所說的那樣,并不是體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結果,科學家們是從代表著不同文化資源的節(jié)目單及字典中去尋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則的。
馬爾凱的文化解釋還在于對科學知識生產(chǎn)的動力學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實際案例,從中做出分析,他的結論是,對于科學實驗結果的意義是什么的評判、對于科學論斷的有效與無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變的標準,在實驗和解釋的過程中,個人的特點、具體的環(huán)境都會產(chǎn)生作用,他說,“科學一致,因而科學知識,并不是僅由證明正確或拒斥來達到的。科學家們經(jīng)常面對的是不確定性和模棱兩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應用事先確立的正式標準來實現(xiàn)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對于研究綱領的拒絕或采納,是一個更加實用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學家的相對具體的旨趣利益影響的。”[8]馬爾凱承認在知識形成過程中,是存在著認識因素的,科學的判斷和解釋是受認識和社會因素影響的。他認為,不僅社會規(guī)范是社會地變化著的,而且對于任何一個研究綱領來說,認識和技術規(guī)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釋的。”在社會意義的磋商和知識主張的評估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社會與技術的公式表述,在具體情況下,是由每個參加者所選定的,所說明的;這兩種資源,在具體科學知識被認可的過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證明程序中,是緊密地綜合在一起的。”[8]
馬爾凱關于科學的文化解釋的結論是:“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已經(jīng)會聚到這樣一種觀念,即把科學看作是一項解釋性的事業(yè),在這個過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又說:“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學知識是由磋商過程確立起來的,也就是被那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對文化資源的解釋建立起來的。在這種磋商過程中,科學家們也運用認識和技術的資源;但最終結果還是依賴于可利用的其他社會資源。因此,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社會結論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特定行動者群體看來是正確的科學主張罷了。”[8]
以上是對科學知識社會學所代表的“人類學轉向”的第一個含義的簡單說明。需要說明的是這個轉向并不是沒有歷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它代表著舊的“知識社會學傳統(tǒng)的復活”,它反映的是“社會和人文科學注意重點的變化和重新取向的過程”。[1]深入的研究將會說明,這種轉向與當代哲學的、社會學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著多種復雜的聯(lián)系,不過,這已不是這篇文章所要討論的問題了。
(二)
人類學轉向的含義之二:對科學作人種志研究
文化是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人類學對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對初民社會(primarysociety)的研究,起源于歐洲和美國的學者對于“不開化的”、非歐洲文化的研究。與人類學的發(fā)展相聯(lián)系,形成了一種主要研究方法,這就是人種志方法(ethnogranhicatmethod)。人種志研究就是對一個特定的民族群體的社會和文化生活進行詳細的描述和分析。這種研究首先要選定地點,即某個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為田野調查(fieldwork)的基地,進行參與觀察,作詳細的記載,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類學著作。許多文化人類學的名著都是人種志研究的成果。這種研究要求有較長的時間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離開以后有時還有通訊聯(lián)系或回訪);這種研究要求研究人員學習當?shù)氐姆窖酝琳Z,盡可能地參與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個觀察者的客觀獨立的立場,除了參與觀察以外,研究人員通常選定或培養(yǎng)某個當?shù)厝俗鳛樾畔⑻峁┱撸╥nformants),等等。這種研究也常常運用比較的方法,對于所研究的文化與其他文化進行對照性的分析。
當代人類學的人種志研究已經(jīng)不再僅僅局限于對于初民社會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會愈來愈少),已經(jīng)發(fā)展到為對現(xiàn)代社會中某個社區(qū)、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對城市中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對于工廠、精神病院、科層制的研究,等等。[10]人種志研究的技術也有很大進展,如廣泛利用電影、錄音、錄像等等手段。顯然,這種方法是可以同樣應用于研究科學活動所在地和科學家人群的。
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的第二個含義:對科學作人種志研究。具體說來,這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代表人物對科學進行的人種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對科學知識持有建構主義觀點的學者,以人類學家的身份進入實驗室,他們以實驗室為田野調查的基地,進行長期持續(xù)的參與觀察,對于實驗室的環(huán)境、儀器設備、科學家的日常活動和對話,對于科學家與實驗室以外的聯(lián)系,以至于科學論文的形成、發(fā)表,論文引證等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詳細的記載,做出分析,寫出研究報告或專著。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現(xiàn)的一批研究成果,它們有一個概括性名稱,即“實驗室研究”(IaboratoryS-ludies)。在這種成果中,除了我們已經(jīng)知道的拉都爾對美國加州薩爾克實驗室的研究、謝廷娜對伯克利大學中生物化學等相關實驗室的研究和這兩項研究的成果《實驗室生活》和《知識的制造》以外,還有若干研究及其相應的成果。[2]雖然這一批著者在他們的進一步分析中表現(xiàn)出差異和分歧,但他們的共同認識是“深入到科學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經(jīng)驗材料,就可有益于對科學的理解”。[11]而謝廷娜則把這一批“實驗室研究”看作是說明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綱領的,她說:“這個綱領是被若干個實驗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爾的《實驗室生活》一書的工作基礎是長達一年零十個月的田野調查,他進入實驗室觀察科學家的日常活動,進行相關研究,他的書內容確實展現(xiàn)了人種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資料:有實驗室場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學家在不同場合的對話記錄,有科學儀器狀況的一覽表,有某項化學物質合成的報告記載,有科學家個人事業(yè)經(jīng)歷的摘要,等等。拉都爾運用這些資料得出了認識論的結論:實驗室是文學標記的系統(tǒng),儀器所顯示的現(xiàn)象是“技術現(xiàn)象”,科學實驗室中的事實是“人工事實”,因而科學事實不是被發(fā)現(xiàn)的而是被制造出來的,科學的陳述是磋商的結果等等。其實,拉都爾在《實驗室生活》的第2版后記中就說過,他在進入實驗室之前就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看法即科學認識是受社會因素制約的,他在參與觀察中的工作只不過是搜集詳盡的材料罷了。這就使得這部運用人種志研究的著作讀起來與其他文化人類學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與分析結論似乎有某種不連貫;這些分析,與其說是文化人類學的,不如說是認識論的,與其說是社會學的不如說是哲學的。
《知識的制造》這部書的特點就更加明顯了。這部以人種志研究為基礎的專著,已經(jīng)完全把調查來的資料編納入作者的認識論結論的框架中了。“科學家作為實踐的推理者:知識是在環(huán)境中建構起來的”;“科學家作為索引性推理者:科學研究的機會主義和情境性”;“科學家作為類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則和革新的隱喻推理批評”;“科學家作為社會環(huán)境中的推理者,從科學同體到跨越科學的領域;”“科學家作為文學的推理者,或者實驗室推理的嬗變”;“科學家作為符號推理者,或‘我們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qū)別’”,這就是該書的章節(jié)標題所構成的框架。這樣,在文化人類學著作中通常見到的對文化現(xiàn)象的完整而生動的描述性記載不存在了,資料“淪為”結論的例證。
在這里,我們不能詳細討論這些結論與哲學、社會學思想的具體聯(lián)系,那是需要專門的研究的。我們在這里要說明的是,科學知識的微觀建構學派是運用人種志研究方法尋找經(jīng)驗資料支持和論證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綱領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不過,我們又可以看到,這個學派的運用,與本來意義上的文化人類學人種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為他們進入了認識的領域,而且是科學認識的領域。拉都爾也承認了這一點,他說,他“所使用的人種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義上與人種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們一方面把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微觀建構學派的“實驗室研究”看作是“人類學轉向”標志;另一方面,從嚴格的人類學意義上考察,又只能把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討論的具體運用。
(三)
科學技術人類學:有待開發(fā)的領域
科學知識社會學所代表的“人類學轉向”,只不過是科學技術研究的人類學取向或者科學技術人類學的一種類型。全面系統(tǒng)論述科學技術人類學,筆者尚力所不及,僅就目前的初步認識,說明以下要點:
(1)科學技術人類學,在嚴格意義上說,應該是訓練有素的人類學家,運用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對于科學技術所作的研究。在人類學領域,早已存亡可以歸納入這個范疇的研究成果,這就是:考古人類學及人種志研究對于含有科技內容的“物質文化”的研究;人類學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識系統(tǒng),為民族數(shù)學(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醫(yī)學人類學所研究的與健康和疾病有關的非西方的知識系統(tǒng)〔3〕,等等。因此,有的學者指示,“在這個意義下,人類學開始研究科學技術,要比跨學科領域STS研究科學技術早得多。”[13]當然,人類學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學,是非西方文明中的傳統(tǒng)科學,并不是現(xiàn)代科學技術。
(2)正因為人類學的研究傳統(tǒng)是關注歐洲以外的文化,所以,在歐洲文明中發(fā)展起來的現(xiàn)代科學技術就必然處在專業(yè)人類學家的研究視野之外。現(xiàn)在,對于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社會研究已經(jīng)發(fā)展為大的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人類學家進入這個領域的仍然為數(shù)不多,為1988年美國的4S’學會召開會議,有來自各學科的學者529人,其中人類學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來畢竟出現(xiàn)了一批人類學取向的科學技術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那么,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絕大部分科學人類學研究或者人種志研究是由社會學家、哲學家及其他并沒有受過社會文化人類學的專門訓練的人完成的。”[14]這樣一些社會學家哲學家在采取了人類學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類學特點的著作以后,就獲得了人類學家的稱號,如拉都爾就是一例。這些不是人類學家(或者說準人類學家)所作的研究,被人類學家看來是存在著某種混亂的,有人指出,“實驗室研究”作為人種志研究的一種版本,是與人類學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爾也談到他的人種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評。[11]
(3)正因為如此,為了更好地發(fā)展這個領域,關心科學技術研究的人類學家的建議是:必須弄清人種志方法的真諦,弄清這種方法的要害在于記和寫(grapy)、在于描述,在于通過寫他們來說明人民和他們的文化;必須了解文化人類學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學者: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整體主義的人種志學,以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的比較主義方法,以格爾茨為代表的符號象征主義的文化解釋學等等。[14]我以為對于當代有重大跨學科影響的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茨及其文化解釋學尤應引起注意。[15]
(4)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做的工作也許是接近于格爾茨的文化解釋學的。如前所述,馬爾凱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對科學進行了文化解釋,埃爾卡納則以專門的章節(jié)論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學史中的運用,討論了科學知識增長、科學與其他文化因素,歷史舞臺上的科學等。但我們沒能讀到埃爾卡納或是馬爾凱都沒有運用人種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體的研究。而“實驗室研究”所作的經(jīng)驗描述的意義在于得出認識論的、哲學的結論,是完全不同的版本。這是因為他們給自己規(guī)定去研究的文化現(xiàn)象,是格爾茨都認為是棘手的問題:科學。格爾茨是有法律實踐經(jīng)驗的學者,他從文化解釋的角度說明了法律現(xiàn)象,但是當他把科學與其他文化現(xiàn)象并列時,卻不止一次地說過:“盡管我們很偏愛科學,但它仍然不失為一種棘手的事務”,“但物理學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識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類學上難以理解的問題。”[16]
(5)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決不局限于對實驗室的研究,可以從實驗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擴展到學術會議上的擴展到法庭中的科學家,[10]這也就是說要“從實驗室走向更為廣闊的和多元的領域。”[13]有的社會學家選擇了科學事業(yè)管理組織及其附屬機構,[17]有的學者進入了政府設立的海洋生物養(yǎng)殖經(jīng)濟研究組織[18]在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點也不單純是科學知識的生產(chǎn)過程,涉及到了這些機構中科學家的社會身份,涉及到實驗室與顧客、科學知識與生產(chǎn)方法以及科學政策和經(jīng)濟組織的關系等問題。特別要揭示的是,同樣進入實驗室,其研究重點也不一定就是科學知識的生產(chǎn),以特拉維克對美國及日本的線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點就是實驗室組織結構,領導風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學工作條件的模式差別。[19]
(6)正是因為如此,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種志的田野調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樣的;發(fā)展一種“跨學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這也就可以包括歷史的研究、比較的方法、文本閱讀、……等方法;并且基于這種種方法的運用,“對于‘科學技術’意義的定義,不可避免地以理解專家到理解非專家。”[13]雖然我們對于上述這些方法也許還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樣性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7)總之,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極為擴散,各具特點,我們只要看看《諸科學與諸文化》(《SciencesandCultures》[1])和《知識與社會第9卷,科學技術學人類學》[13]這兩部文集的論文題目就可以知道了。每個作者都按照自己對于人類學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點,進行不同的人類學探討。研究這些以及其他科學技術人類學的論著,要在紛云繁復的論述中弄清來龍去脈把握要害,我認為,有一項工作要做,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關鍵概念,諸如“人工事實”、“技術現(xiàn)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結構的和形容的”(emveandetic),等等:它們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點,了解除它們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談到實驗室的人種志研究的時候,不能不提到對實驗室的民俗學研究,這就是社會學中民俗學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4〕代表人物加芬克爾及其學派的工作。麥克爾·林奇把這一批研究稱之為“對科學工作的民俗學方法論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studiesofscientificwork),指出這種研究要詳細考察實驗室中“自然地組織起來的日常活動”“討論”有關實驗室工作的暫時的秩序”[20]。他并且專門著書論述了民俗學方法論與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的關系。[21]那么,這種研究與前述人種志研究有什么關系?在民俗學方法識者看來,人種志研究是與“民俗學方法論的文獻是有密切關系”的,甚至認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學方法論的說明者”[20];而人種志研究的學者則認為民俗學方法論是人種志研究的一種。[10]弄清這兩種研究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決不是輕而易舉的工作。我們要指出的是,從已有的人種志研究的著作來看,他們確實從民俗學方法論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這一點,對于認識知識社會學微觀研究的特點也許是重要的。
(9)最后要說的是,科學技術的人類學研究中的專業(yè)人類學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類學背景研究人員仍然會占相當大的比重。因為,專業(yè)人類學家即使轉向現(xiàn)代社會生活的廣大領域,能夠專門研究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也畢竟是少數(shù)。這種情況,對于在人類學科并不充分發(fā)展的中國從事于科學的社會研究的學者來說,也許是一種機會:他們也許可以增添幾分勇氣,去涉足這個確實頗為陌生的文化人類學的研究領域。
注釋:
〔1〕人類學是一個大的綜合性學科,包括有體質人類學、考古人類學、語言人類學、社會(或稱文化)人類學等分支學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會(文化)人類學。
〔2〕ethnography另一種譯法是民族志,我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書》的中文版的譯法。
〔3〕1996年我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特爾多)人類學系講學時,就見到一位研究藏醫(yī)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作田野調查。
〔4〕這個詞在社會學中有多種譯法,如:民俗學方法論,人種方法論。
〔5〕從兩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這一點:1992年出版的《知識與社會》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類學家;而1982年出版的《諸科學與論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類學家。
【參考文獻】
[1]WotgeLepenics: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sinthesociologyofscience,in"SciencesandCultures",EditedbyE.MendelsonandE.Elkana,D.ReidelPublishingCompang,1981,p.245,p253.
[2]KarinKnorr-Cewua:"TheEthnographieStudyofScienelifieWork:TowardsaConstractivislInterpretationofScience,in"ScienceObserved",EditedbyR.Knorr-CentinaandM.Mulkay,SagePublicalionLtd,1983.p.115,pp.117—118.
[3]YehudaElkana:AProgrammaticAuemttatanAnthronologgofKnowtedgein"SciencesandCultures",P.6.
[4]克利福德·格爾茨:《深描:向文化解釋學理論》,《國外社會學》1996年1—2期,P.40.
[5]BarryBarnes:ScientigieKnowtedgeandSociologicdTheory.RoultedgeKeganPaulLtd.1974.p.63.
[6]DavidBloor:ScienceandSocidlImage,RonteedgeKeganPaul&fd.1976,pp.4—5.
[7]DavidBloor:Wettgenstein-ASocialTheorgofKnontedge,MacmillanEducationLtd.1987.p.83.
[8]MichaelMulkay:ScienceandtheSociofogrofKnonfedge,GeorgeAllenandUnwinLtd.1979,pp.68—95.
[9]Ethnography,BritanicaVoi.4,pp.583—584.
[10]R.S.Anderson:TheNecessaryofFieldMethodinFliedgmmethodofScientificRecearch,in"ScieneesandCutlures,p.218,p.216.
[11]BrunoLalour:LaboralorgLifePrincetonUnicversityPress,1986,p.278.
[12]KarinD.Knorr-Cetina:TheMonut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13]"Precoce",in"KnontedgeandSociety:theAnthropologyofScienceandTechnology,Vol.9,1992,"JALPressInc.p.x.
[14]DavidJ.Hess:"Introduction:ThenewEthnographyandtheAnthropolog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ibid,pp.1—17.
[15]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韋伯、帕森斯、格爾茨》,《國外社會學》,1996年1—2期,pp.106—110.
[16]格爾茨:《地方性知識》,《國外社會學》1996年1—2期,p.91,p.93.
[17]SlacieE.Zabushy:"MultipleConlexts,MultipleMeaning:ScientistintheEuropeaSpaceAgency,in"KnowledgeandSociety,Vol.9.".
[18]M.CollonandJ.Laws:"OntheConstructionofSocio-techniceeNetworks:ContentandContextRevisited",in"KowlegeandSociety,Vol.8,1989SludiesintheSociologgofSciencePastandPreseut,JALPressINC.
[19]KarinKnorr-Cetina:"LaboratorySludiesandTheConstructionApproachintheStndyofScinceandTechnologg,(日)《科學·技術·社會年版》1993、卷2p.138.
對文化人類學的看法范文第2篇
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地被稱為哲學家、政治經(jīng)濟學家,除了馬克思對“社會學家”的標簽不感興趣外,他們更極少被成為人類學家。然而,馬克思與查蘇利奇關于俄國農(nóng)村公社的通信,馬克思描述前資本主義社會歷史形態(tài)的《人類學筆記》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都進入過人類學文獻。《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實際上是建立在馬克思有關筆記的基礎之上———是馬克思計劃寫而未能去寫的著作,事實上他的逝世使他壯志難酬;馬克思對人類學的關注,成為他學術研究的中心,直到他生命的終結①。人類學歷史上,懷特(Leslie White)寫了一系列文章,與博厄斯為首的歷史特殊主義論爭,認為社會演化有其普遍規(guī)律。懷特還復活了摩爾根的進化論類型學。盡管懷特沒有提到馬克思的名字,但一般認為,懷特理論的調子是;馬克思強調勞動力和生產(chǎn)資源,懷特則以對能量的控制取而代之,認為后者是人類演化的決定力量②。人類學家閱讀和討論馬克思、恩格斯似乎言之有據(jù)。國內學者對這一點也有所認識。陳慶德指出,馬克思理論體系不僅對經(jīng)濟人類學有認識論上的啟示意義,而且其經(jīng)濟分析也直接為經(jīng)濟人類學開辟了學科道路③。陳建憲也注意到,馬克思放棄《資本論》的寫作,轉而閱讀大量的文化人類學著作,從政治經(jīng)濟學轉向了文化人類學研究④。羅力群也對文化唯物主義認識論原則、理論原則做了縝密梳理⑤。通過回顧和檢視近百年來的相關重要文獻,筆者試圖突顯和強化以下看法:“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不認為自己是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他們轉向人類學和歷史,與其說是要關心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本身,不如說要對資本主義進行分析。……他們往人類學那里繞一下彎,就是為了要證明這些概念的靈活性、暫時性和相對性。”①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觀、方法論和認識論是人類學唯物主義傳統(tǒng)的理論源泉,尤其是哈里斯文化唯物主義知識與智力的來源,從而成就了在人類飲食研究領域別具一格的研究策略。
一、從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立場到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策略
哈里斯研究工作的理論前提是,“人類生活是對其生存實際困境和難題的反應”;他也名副其實地宣稱,“盡管不是我發(fā)明創(chuàng)造了‘文化唯物主義(cultural materialism)’,但確是我給這個概念賦予了意義”②。他認為,范式(paradigm)是一個容易引起分歧的概念,他主張以研究策略(re-search strategy)取而代之,而這種研究策略有其唯物主義依據(jù)。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chǎn)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著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③如果說文化唯物主義有一套相互關聯(lián)的理論原則,哈里斯認為,馬克思的這段話富有先見地闡明了這些原則的核心;這一偉大原則是人類知識史上的一個重大進展,其意義和價值與同時代華萊士和達爾文表述的自然選擇原理不相上下。但從現(xiàn)代人類學的角度看,“生產(chǎn)方式”用語具有認識論上的模糊性,對“再生產(chǎn)方式”的疏忽,以及缺乏對主位與客位、行為與思想的區(qū)分,都極需要重新給予闡明④。對人口再生產(chǎn)方式中技術和手段的忽略,“未能賦予人口控制的技術發(fā)展在文化演化中以中心作用,極大地傷害了經(jīng)典和新潮的原則和理論的可信性”⑤。對文化唯物主義研究策略的理論闡明始于客位、主位之分。在哈里斯看來,每一社會必須解決生產(chǎn)問題———在行為上滿足最低限度的生計需要;因此必須有一種客位(etic)行為的生產(chǎn)方式。
其次,每一社會必須在行為上解決再生產(chǎn)問題———避免人口出現(xiàn)破壞性的增長或減少,因此必須有一種客位行為的再生產(chǎn)方式。再其次,每個社會必須處理好一個必要問題,即保證組成社會的各個團體之間、與其他社會之間安全、有序的行為關系……行為的上層建筑是這種普遍反復出現(xiàn)的客位方面的合適標志⑥。主要的客位行為包括以下類別:(1)生產(chǎn)方式:用于擴大或限制基本生計生產(chǎn)的技能和實踐活動,特別是食物和其他形式的能的生產(chǎn),假使特定的技能與特定的居住地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限制和機會。具體包括生計技能,技術與環(huán)境的關系,生態(tài)系統(tǒng),工作模式。(2)再生產(chǎn)方式:用于擴大、限制或保持人口數(shù)量的技能和實踐活動。具體包括人口統(tǒng)計及其模式的醫(yī)學控制,配偶方式,生育力、出生率、死亡率,育嬰,避孕、墮胎、溺嬰。(3)家庭經(jīng)濟:在宿營地、住宅和公寓或其他家庭住地內組織的基本的生產(chǎn)、交換、消費和再生產(chǎn)。包括家庭結構、家庭分工、家庭社會化、家庭紀律與性角色等⑦。其中,生產(chǎn)方式和再生產(chǎn)方式歸入基礎結構,家庭經(jīng)濟和政治經(jīng)濟歸入結構。(4)政治經(jīng)濟:在群體、村落、酋幫、國家之間的生產(chǎn)、交換、消費和再生產(chǎn)。藝術、音樂、舞蹈、文學、儀式、戶外活動、游戲、業(yè)余愛好等被列入行為的上層建筑。
這樣便得到了基礎結構、結構和上層建筑的三重方案。與這些客位行為大致相應的一套思想則分別是:(1)生計知識、民族動物學與植物學;(2)親屬關系、種族關系;(3)象征、神話、審美與哲學等①。文化唯物主義對馬克思原則的理論表述可以概括為:客位行為的生產(chǎn)方式和再生產(chǎn)方式,蓋然地決定客位行為的家庭經(jīng)濟和政治經(jīng)濟,客位行為的家庭經(jīng)濟和政治經(jīng)濟又蓋然地決定行為和思想的主位(emic)上層建筑。可以簡潔地稱之為基礎結構決定論原則②。把再生產(chǎn)方式標入基礎結構,就能闡明一套有創(chuàng)見的、首尾一致的可檢驗的重要理論③。文化唯物主義策略還基于扎實的實證研究。自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哈里斯就“對主張多實地調查、少閉門造車的研究方法極感興趣”④。他曾在巴西、莫桑比克、印度、厄瓜多爾和紐約等地從事田野工作,以充分的經(jīng)驗資料和社會事實為依據(jù),證實了他的發(fā)現(xiàn)。哈里斯從人口、技術、環(huán)境、生育控制等因素著手,檢視了采集狩獵社會前后的社會變遷,其嚴密的論證和有力的事實證實了馬克思的以下兩個著名論斷⑤:“社會的物質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xiàn)存生產(chǎn)關系或財產(chǎn)關系(這只是生產(chǎn)關系的法律用語)發(fā)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形式變成生產(chǎn)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⑥“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chǎn)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chǎn)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xiàn)的。”⑦哈里斯反對那種把文化視為純粹主位現(xiàn)象和個體精神、思想活動的看法。對于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哈里斯認為這是一套研究思想、上層建筑的原理,雖然是西歐影響最大的人類學研究策略,但它是反實證的、反辯證的、唯心的和無視歷史的⑧。包括本尼迪克特在內的心理人類學家先驅們提出,人格構型是社會生活中穩(wěn)定的、經(jīng)久不變的核心。而文化唯物主義的核心觀點則是,基礎結構和結構的根本改變能在極短的時間里導致人格構型的徹底逆轉⑨。認知主義則在主位規(guī)則的知識基礎上預測客位行為瑏?瑠,而文化唯物主義的選擇也比弗洛伊德的選擇更為可取?瑏瑡。重要的是,哈里斯通過在各地開展的扎實的田野工作,證實了文化唯物主義策略的說服力,展示了其在多種研究策略中的優(yōu)勢。#p#分頁標題#e#
二、飲食的奇風異俗:豬肉、昆蟲及其他
人類社會的飲食現(xiàn)象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奇特習俗和傳統(tǒng)。Robert Rowie喜歡收集此類資料,并稱之為人類飲食習慣中“變化無常的非理性事件”。飲食人類學展示給人們的是,在特定的社會、文化和民族中,吃什么,不吃什么,怎么吃,人們飲食偏好背后的規(guī)范和機制。比如,存在這些飲食禁忌: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不吃豬肉,印度教不吃牛肉,美國人不吃馬肉、山羊肉和狗肉;也有看似怪異的飲食偏好,馬肉是法國人和比利時人的美味,大多數(shù)地中海沿岸居民喜歡吃山羊肉,蛆蟲和蚱蜢在更多的社會里被當做美食①。問題是,這些飲食的背后有多少營養(yǎng)學的因素?多少遺傳學的因素?多少消化生理學的因素?多少環(huán)境生態(tài)學的因素?多少區(qū)域人口學的因素?多少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因素?這些因素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面對差異迥然的飲食習俗,哈里斯贊同“談到口味無爭辯”的文化相對論主張,不應當責難或譏笑不同的飲食習慣和風俗。但依然留下許多值得討論和深思的問題。哈里斯關心的問題是,人類的飲食方式為什么存在這么大的差異?人類學家能否解釋為什么在這種文化而不是別的文化中發(fā)現(xiàn)了某些食物的禁忌和偏愛?
哈里斯指出,人類學存在三種解讀方法:文化唯心主義、折中主義和唯物主義。有學者主張,不應當?shù)绞澄锏捻椖啃再|中去尋找,而是到人們的基本思維模式中尋找。文化唯心主義者,如列維斯特勞斯認為,自然物種被選擇,不是因為它們是“好吃的”,而是因為它們是“好想的”,另外一些食物則是“不好想的”②。“在道格拉斯看來,人類學家研究飲食方式的主要任務是解碼它們所包含的神秘信息。對古代以色列人的豬禁忌,不必研究自然史、考古學、生態(tài)學、豬的營養(yǎng)價值和生產(chǎn)豬的經(jīng)濟學。折中主義表面上站在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立場之間,實際上有這樣的強烈傾向:對具體的飲食方式個案做唯心主義的解釋。”③。法國人類學家Fischler表達了一種流行的看法:“當我們觀察與人類飲食習慣相關的象征和文化表現(xiàn)時,只能接受如下事實:其持久性和頑固性是任意的原因造成,其中大部分很難講出什么道理來。”④這種論點則顯然流于不可知論。哈里斯的視野總是同更加廣闊的經(jīng)濟、人口、環(huán)境、生態(tài)、地理等因素聯(lián)系在一起,揭示了飲食禁忌與偏好的“文化之謎”,認為“食物是否有益于思考取決于它們有利于吃或不利于吃。食物必先填飽群體的肚子,然后才充實其精神”⑤。
猶太教《舊約》借上帝之口規(guī)定不可吃豬肉。1859年醫(yī)學發(fā)現(xiàn)旋毛病與烹煮不夠的豬肉之間的臨床關聯(lián),被神學家用來為《舊約》食物禁忌辯護。哈里斯把禁忌產(chǎn)生和發(fā)生作用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自然地理狀況作為考察的重點,得出這樣的結論:中東地區(qū)的氣候和生態(tài)環(huán)境不適合家豬飼養(yǎng)而有利于反芻動物(牛、羊)飼養(yǎng),古代以色列人迫于成本和收益比較的生存壓力和人口壓力,不得不放棄曾有的養(yǎng)豬生產(chǎn)。現(xiàn)代的歐美人不吃昆蟲,認為它們有細菌、骯臟、令人生厭。事實上,人類的祖先是吃昆蟲的。中世紀以來,歐洲人也吃昆蟲。哈里斯指出,從營養(yǎng)學的角度說,昆蟲幾乎和紅肉、家禽一樣有營養(yǎng)。昆蟲攜帶的細菌可以通過烹煮殺死。回答現(xiàn)代歐美人為什么不吃昆蟲的問題,必須檢驗吃昆蟲或其他小東西的比較成本和效益。他以生態(tài)學的最優(yōu)化覓食理論預測:狩獵者和采集者將只尋覓和收獲相對于“處置時間”(追尋、殺死、運載、烹煮等)能得到最多卡路里回報的物種;只要新項目增加了覓食活動的總效率,該項目就會被添加到他們的食譜中。哈里斯說,歐美人有足夠的牛肉、羊肉、禽類和魚肉,連馬肉都看不上,怎么會需要昆蟲呢?
三、印度圣牛之謎
印度擁有十億人口,需要大量的蛋白質和熱量來維系如此眾多民眾的生命和健康。因為食物不足,印度人口曾普遍遭受饑餓和營養(yǎng)不良①。但同時,印度大量的活牛或將死的牛不被人宰殺為食。吃慣了牛肉的歐美人可能大惑不解,因為看似非常不合理性的情景確實存在:印度人禁止宰殺牛作食物吃掉。國家政策的指導性條文第48款規(guī)定:“禁止屠殺母牛和牛犢,以及其他產(chǎn)奶和駝物的動物。”印度有兩個邦通過了“牛保護”法案。因為沒有人宰殺牛肉吃,印度擁有全世界最多的家畜,即大約1億8千萬頭牛;也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游走于田野、公路、街道上的老弱病殘之牛②。
印度人為何如此保護牛、回避吃牛肉、飼養(yǎng)大量無用的家畜?一個重要的解釋把它歸結為宗教狂熱:這里的主流宗教印度教的核心教義是牛崇拜和牛保護。印度人崇拜他們的母牛(和公牛)為神靈,在家中飼養(yǎng)它們,給它們起名字,同它們說話,用花環(huán)和綬帶裝飾它們,容許它們在繁忙的大馬路上信步游走③。母牛還成為政治的象征,母牛和牛犢的圖畫曾被國大黨當作國家的標志④。但是,無論是宗教還是政治都無法解釋:為什么殺牛和食用牛肉成為首選的象征?為什么是牛,而不是豬、馬、駱駝或別的動物?哈里斯指出:“我不懷疑神圣母牛的象征性力量。我所懷疑的是,在一種特殊的動物種類和一種特殊的肉類的象征力量之認定,是出于任意的、隨機的精神選擇,而不是出于一種確定的實際限制。”⑤通過對印度宗教爭斗、農(nóng)民生活、人口變遷等方面歷史的細致考察,哈里斯發(fā)現(xiàn):印度農(nóng)業(yè)體系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為了吃肉而屠殺了在能量和營養(yǎng)上更有用的動物,而禁止殺、吃牛肉的宗教戒律則有助于該問題的解決。“圣牛(sacred cow)”的宗教及其信仰和觀念畢竟是一定基礎結構(人口壓力、自然環(huán)境壓力和技術發(fā)展水平等)之上的實現(xiàn)最優(yōu)化要求而產(chǎn)生、興盛的。由于這種基于歷史資料的研究,哈里斯也顯現(xiàn)出濃厚的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旨趣。正如羅力群所說,對圣牛個案的分析,頗有經(jīng)典著作的味道,校正了“好吃”的偏頗、謬誤和淺薄⑥。
具體而言,哈里斯所看到的,婆羅門信徒們選擇了一種更富于生產(chǎn)力的農(nóng)耕體制:強壯有力、肩背上有瘤的大牛能夠在炎熱、干旱和其他不利條件下充當拉犁動物,而它們消耗的飼料很少。由于這些牛很少(像歐美那樣)在人工種植的草場上放牧,也不在人類生產(chǎn)糧食的田地中放牧,所以,幾乎不可能在資源方面與人形成競爭。這些家畜在工作之前處于半饑餓狀態(tài),在犁地的間歇期吃植物的主莖、谷殼、樹葉和家庭的剩飯剩菜。耕作期間,它們吃人類吃不動的棉花籽兒、黃豆和椰子的殘渣壓制的油餅。在印度的大多數(shù)地區(qū),用家畜從事糧食生產(chǎn),每單位的成本收益要比使用(像美國情境下)拖拉機更高一些。它們可以在抗病力強、耐力佳的狀態(tài)下工作12年之久。牛糞是印度最大的有機肥料,也是清潔、可靠、無氣味的熱源,缺乏木質和化石燃料的千萬家庭就靠它燒火做飯。母牛比公牛還有清道夫的優(yōu)勢:麥稈、谷殼、路邊雜草、樹葉和人類不能消化的其他東西都被它吃掉,更不用說它的奶是有價值的副產(chǎn)品了⑦。總之,活牛在印度人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母牛和公牛是一種成本很低的耕作工具,可以在很多方面替代拖拉機;牛的糞便既可以當作肥料,也可以作燃料;印度的牛以草為飼料,它們不像在美國那樣與人爭奪糧食,這樣它們提供的肥料和燃料就是免費的,而美國則不缺乏木材、石油和煤炭。更為重要的是,只需少量飼料和水,牛就能夠在印度那樣燥熱的氣候條件下存活很長時間。如果為了饑餓的緣故就殺牛,在印度人看來是很不合算、不應該的,因此自然產(chǎn)生了一種“愛牛情結”。總之,印度教的意識形態(tài)所起的作用服從于由生態(tài)、政治、經(jīng)濟和其他的行為和客位的條件所加的種種限制①。#p#分頁標題#e#
對文化人類學的看法范文第3篇
民族志(ethnography)作為民族學重要的組成部分,完整地表現(xiàn)了人類學家田野調查的記錄、描述、分析和解釋。但是,民族志無論作為一種學科的原則,還是調查的方法,抑或是人類學家書寫的“作品”,不同時代、不同學派的人類學家都有著不同的主張,這也構成了人類學重要的歷史內容。
古典人類學家弗雷澤在他的代表作《金枝》中,為人們講述了一個關于古羅馬狄安娜的神話原型在意大利尼米湖地區(qū)的儀式敘事:在當?shù)貜R宇有一棵神圣樹,便是傳說中的“金枝”。它由獲得“森林之王”稱號的祭司守護著,任何覬覦者若能在與祭司的爭斗中殺死他,便可得到祭司之位和“森林之王”的稱號。所以,它便成了“決定命運的金枝”。這一神話敘事不僅經(jīng)歷了從克里特到意大利半島的地理遷移,也經(jīng)過了不同國家、族群長時間傳承的變化;然而,其原始基型仍屬神話的敘事范疇,即它并不是歷史事實,而是以一種神話傳說式的敘事類型來解釋祭祀儀式的起源。弗雷澤以此神話儀式為原點,從世界各地同類型的口述和文獻資料的比較中發(fā)現(xiàn)了巫術和宗教的規(guī)則與原則,即著名的“相似律”與“接觸律”,它們同屬于“交感巫術”范疇。毫無疑問,《金枝》是一部偉大的人類學作品,在很長的時間里,它在“民族志”的概念和敘事范式的討論中既受推崇,也受質疑。這一切都與民族志在不同時代所遵循的原則有關。
民族志作品被視為人類學學科的產(chǎn)品和“商標”已屬共識。從寬泛的意義上說,民族志研究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lián)的部分:第一,人類學家對研究對象進行現(xiàn)場性“參與觀察”,即所謂“田野調查”;第二,民族志者在調查的基礎上進行描述性文本寫作。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志表述主要體現(xiàn)為“文字文本”,即“志”的書寫記錄。眾所周知,傳統(tǒng)的民族志素以“科學”為圭臬和標榜。早在19世紀的初、中葉,人類學就被置于“自然科學”的范疇,被稱為“人的科學”。馬林諾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除了確立“科學人類學的民族志”的原則外,更對民族志方法(諸如搜集和獲取材料上“無可置疑的科學價值”)進行了規(guī)定,并區(qū)分了不同學科在“科學程度”上的差異。美國“新進化論”代表人物懷特堅持人類學學科誕生時所秉承的“進化論”和“實驗科學”學理依據(jù),進一步地確認民族志為“文化的科學”。由于人類學屬于“整體研究”(whole),因此,總體上可歸入“形態(tài)結構的科學”范疇。然而,對人類學的“科學”的認定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不言而喻的爭議性,無論是就科學的性質抑或是敘事范式而言都是如此。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1)在民族志中,原始的信息素材是以異文化、土著陳述、部落生活的紛繁形式呈現(xiàn)在民族志者面前,這些與人類學家的描述之間往往存在著巨大的距離。民族志者從涉足土著社會并與他們接觸的那一刻起,到他寫出最后文本為止,不得不以長年的辛苦來穿越這個距離。但是,民族志者個體性的“異文化”田野調查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填平“主觀因素”與“科學原則”之間的距離?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迄今為止仍見仁見智。(2)“文獻文本”屬于文學性表述,尤其是最近幾十年,民族志的“文學性”(比如文學的隱喻法、形象表達、敘事等)影響了民族志的記錄方式――從最初的觀察,再到民族志“作品”的完成,到閱讀活動中“獲得意義”的方式。因此,“寫文化”(Writing culture)便成為民族志無法回避和省略的反思性問題。
對于第一個問題,即人類學家對民族志田野的“敘事范式”,在20世紀初、中葉,經(jīng)過連續(xù)兩三代社會科學家們的努力,已經(jīng)形成并得到公認。田野調查基于較長時間(一年以上)的現(xiàn)場經(jīng)歷,這對于一般民族志研究而言已得到了普遍的認可。比如早期的民族志研究都以如下案例為典范:博厄斯在巴芬島愛斯基摩人中為期兩年(1880-1882年)的調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在印度洋安達曼島上兩年(1906-1908年)的研究;以及馬林諾夫斯基在美拉尼西亞東部的特洛布里安島上四年的研究(1914-1918年)等。但對于人類學家在田野調查中“主體的對象化”問題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過分“自我的他化”可能被認為是“植入其中”或“淪為研究對象”,從而導致“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主體性迷失;另一方面,深陷其中的人類學家可能因此減弱對客觀性把握的能力,甚至減退研究的熱情。盡管如此,長時間的田野調查畢竟可以保證民族志者與被調查對象朝夕相處,深入到他們生活的內部。這些都屬于民族志研究參與體認的原則范疇。因此,田野調查的“參與觀察”作為社會人類學的基本原則并未受到根本的質疑和改變。按照帕克(Park)的說法,這種研究原則和方法有別于“圖書館式”的研究原則和方法,帕克將其形象地描述為“在實際的研究中把你的手弄得臟兮兮的”。據(jù)此,民族志者亦被戲稱為“現(xiàn)實主義者”。
第二個問題,即“文獻文本”屬于文學性表述,較之第一個問題則完全不刷:雖然在表面上它屬于“表述”范疇,但由于它不僅關乎民族志者經(jīng)過“辛勞”獲得的資料在“真實性”上是否被認可,而且關乎人類學家在身份上屬于“科學家”抑或“作家”的問題。從歷史上看,文化人類學的先驅們曾熱衷于將自己視為“文人”(men-of-letters),如弗雷澤、泰勒、哈里森、雷納、穆勒、史密斯等;或者干脆把人類學當作研究語言和文學的科學。這些打著“科學”旗幟的先驅們中的一些人,也因同樣的原因被人譏諷,比如弗雷澤便被其晚輩戲稱為“太師椅上的人類學家”。然而時過境遷,當代一批有影響的人類學家,如克利夫?格爾茲、維克多?特納、瑪麗?道格拉斯、列維-斯特勞斯、愛德蒙?利奇等都對文學理論和實踐感興趣。至于早期的人類學家們,像瑪格麗特?米德、愛德華?薩丕爾、露絲?本尼迪克特等,既是人類學家,同時他們也把自己視為文學藝術家。“文學”在這里不只是對一個藝術門類的言說,也不只是指人類學家們的“田野作業(yè)”和民族志研究中所面對的“文本”(literary texts)類型,更為重要的,它涉及到同樣作為“作者”(author)在確定什么樣的材料能夠進入他們民族志中的“主觀性”問題以及對所謂的“表達”范式的選擇。這種被稱為“實驗民族志”的目的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了達到文化的自我反省和增強文化的豐富性。說到底,民族志范式的變革與當代的知識革命密不可分。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正視,即我們討論的“文學的文本”,尤其是民族志的“文學性”,已經(jīng)遠遠超出好的寫作或獨特風格的范圍。當文字性的表述方式成為一種權力的時候,對文學表述形式的理解和解釋必定是“過度性”的。就像一個人一俟處于“位高權重”時,對他的溢美之辭必定“過譽”。事實上,位置的權力構造遠比位居其上的人更重要。同樣,某一種表述方式的權力化與歷史語境的“話語”有關。安德森認為,在民族國家建立的歷史過程中,資本主義、印刷利,技與人類語言的多樣性三者結合,使這一“想象共同體”即現(xiàn)代新型國家的出現(xiàn)成為可能。可以這樣說,文字書寫構成了現(xiàn)代國家預先搭建舞臺的一個基樁。在很大程度上,“寫 文化”是國家權力在敘事方式上的一種延伸。所以,我們今天對民族志“寫文化”的討論表面上針對的是一種敘事方式,本質上卻在反思建構這一敘事背景的政治語境和權力構造。
二、“事實之后”:一種民族志解釋的思辨
格爾茲在《事實之后》(After the Fact)一書中,以民族志者面對不同的“異文化”場景和長時間“事實”變遷為題,以現(xiàn)代性的視野開宗明義:“讓我們設想一下:當一個人類學家在四十年間卷入到兩個地方的事務,一個是東南亞的村鎮(zhèn),另一個則是北美邊陲的村鎮(zhèn)時,你會說它們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你會對那些變化進行對比,描述當?shù)厝嗣襁^去的生活和現(xiàn)在的形貌。你會以一種敘事方式,即以故事來講述事物之間的關聯(lián)性:從一種形態(tài)變到第二種形態(tài),再成為第三種……問題是,事物越是變化,距離它最初的形象和想象就越遠。然而,描述所面對的各種事物、現(xiàn)象以及它們的變化卻是人類學家的常規(guī)性工作。”人類學素以標榜“人的研究”、“關于人的科學”為原則,可是在具體的民族志研究中,民族志者的操作性常規(guī)卻建立在對特例的、混雜的、陌生化、變化的事物或事件的觀察之上,包括諸如青春期通過禮儀、禮物的交換、親屬制度的術語及范圍等,使之介于觀察對象與觀察者之間混雜的形象塑造與形態(tài)描繪中。它既非方法論,亦非主觀性可以準確地把握與界定。二者之間相互滲透與影響使分類和認知產(chǎn)生了借位。換言之,民族志者在“客觀事實”的觀察、認知以及表述中必定包含了對“事實”的選擇和解釋的“主觀性”因素。
以傳統(tǒng)的觀點,一部合格的民族志,除了遵循“參與觀察”這一田野作業(yè)的原則外,還要盡可能地表現(xiàn)出“當?shù)厝说挠^點”。這構成了現(xiàn)代民族志與古典民族志的一個分水嶺,也構成了馬林諾夫斯基與自己的老師弗雷澤之間一個顯著的區(qū)別。兩代人類學家在秉持“科學”原則、搜集資料以及寫作風格上都有迥異的差別。比如在使用以往那些行政官、傳教士、商人或旅行者們的文獻和口述材料時,弗雷澤是欣然接受的。《金枝》主要正是靠這些材料說話。而馬林諾夫斯基則認為,那些材料是不可靠的,因為那些提供材料的人“缺乏專業(yè)訓練”,存在著“先入為主的判斷”,過于“務實”,“與追求事物的客觀性和科學性的觀點不相容”。如果說弗雷澤與馬林諾夫斯基都建立了屬于他們那個時代的民族志里程碑,那么到了格爾茲那里,馬林諾夫斯基的“科學民族志”、“功能主義”以及沉溺于“追求事物的客觀性”的范式也成為一個被跨越的門檻。就像當年“跨越”他的“老師”那樣,馬林諾夫斯基同樣被晚輩所“跨越”。
有意思的是,以格爾茲為代表的解釋主義人類學在堅持“田野作業(yè)”的基礎上,對各類文學文本、口述材料等持相對寬容的態(tài)度。原因是:在他們眼里,“田野”和“文本”都屬于同性質的“事實”,而重要的卻是對事實的“解釋”。換言之,“田野/文本”的關系顯然形成了對現(xiàn)代人類學基本理念的又一次挑戰(zhàn),也就是說不認為它們構成絕對的二元對峙關系,甚至認為二者具有并置的同一性。在這里,“解釋”才是終極性的。格爾茲在《文化的解釋》一書中曾有過一段人類學者耳熟能詳?shù)木訇U述。他認為人類學家撰寫民族志,與其說理解民族志是什么,莫如說所做的是什么,即人類學家以語言為媒介,以知識的形式所進行的人類學分析。他借用賴爾(Ryle)的“深層描繪”展開討論,以日常生活中的“眨眼”為例生動地說明解釋與描述的多重性和意義的多重性,即“眨眼”的事實只有一個,意義卻是多種多樣的:可能是純粹生理性的,可能是對某一個人的故意行為,可能是在特殊語境中意義結構的表述。所以“眨眼”的事實與意義有著不同的解釋。他的結論是,綜觀社會行為的象征王國――藝術、宗教、意識形態(tài)、科學、法律、道德,諸如此類,人類學家并不是以追求客觀王國的形式置身其中,而是以自己獨特的解釋介于其中。
在談到人類學家作為主體解釋的自由與搜集客觀材料的使命時,格爾茲認為,人類學家在其完成的作為文本的民族志里,使人信服的并不是經(jīng)過田野調查得來的東西,而是加入了民族志者的主體性意見,像作者一樣“寫”出來的東西。甚至直截了當?shù)貙⑼恰白髡摺钡娜祟悓W家與文學家放在一起去強調“作者功能”(author function)。由于以格爾茲為代表的解釋人類學對“作者解釋”作用和意義的強調,對傳統(tǒng)人類學研究一味只管最大限度地在“田野作業(yè)”中將人類學家自身當作簡單的“照相機”無疑起到了矯正的作用;并將民族志范式與“寫文化”同置一疇,同時也為古典民族志做了一個新的、帶有“昭雪”意味的申辯與聲援。
不言而喻,民族志研究可以歸入“實踐科學”的范疇;但是,民族志批評對于“實踐科學”的辨識顯然并不局限于單一性地對客觀事實的搜集。如果那樣的話,任何民族志對“異文化”的描述都不及原住民來得細致和完整,任何一位人類學家對某一個地方性民族的了解都不如被了解對象自身,人類學家所做的描述也不及“地方志”工作人員細致和全面。從計量學的角度看,一個只要掌握書寫能力的“當?shù)厝恕保瑢τ凇爱數(shù)厥虑椤钡挠涗浛隙ū榷唐谏钤谀抢锏娜祟悓W家的記錄要清晰、詳盡。我們之所以不認可簡單地從計量學上進行判斷,是因為民族志作為“實踐科學”,原則上要求人類學家保持與對象的“距離”。換言之,“客觀記錄”并非民族志敘事的全部,甚至未必是最根本的一種途徑。
基德爾(Kidder)曾經(jīng)就實踐科學在探索社會奧秘的方法與途徑上的多種可能性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實踐科學屬于許多探索社會領域方法中的一種。實踐藝術和宗教則屬于其他的方法。我們?yōu)槭裁匆獙W習這些方法?它們何以成為實踐科學?一個理由是這些方法有助于正確地判斷人民和民族的表現(xiàn)形態(tài),預測他們的未來。另一個理由是它們有助于理解社會生活中的事物,發(fā)現(xiàn)與這些事物相關聯(lián)的脈絡以及形成相互關系的原因。也就是說,這些方法不僅使人們了解到事物、預測事物演變的方向,而且對這些現(xiàn)象做出解釋。第三個理由是有助于控制事件并使之產(chǎn)生人們期待的效果。”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類學家在田野作業(yè)中努力采用“實踐科學”的方法和手段,以獲得客觀事實的科學性;另一方面,他們針對客觀事實所做出多樣性、個性化的解釋。
文本可以類同于一種敘事。敘事經(jīng)常被比喻為故事的講述。人總介入于“故事”之中。理查德森認為,人類的本質有多種表現(xiàn)形式,除了人的“生物存在和經(jīng)濟存在”之外,還有一個基本的屬性,即“講故事者”(storyteller)。它表明,“社會人”總脫離不了社會和歷史的情境。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都在故事之中,同時故事又確認人的講述時態(tài)與語境。人是故事的制造者,故事又使人變得更為豐富;人是故事的主角,故事又使得人更富有傳奇色彩;人是故事的講述者,故事又使人變得充滿了想象。在這里,敘事本身具有自身的功能一結構性質。格爾茲試圖通過“事實之后”的命題告訴人們,獲得“事實”不是最重要的,“事實”包含著闡發(fā)的多種可能性,那才是至關重要的。另外,我們有必要強調,“敘事文本”也是一種客觀性的物質存在。文本成為“文字類型的表述”也會產(chǎn)生類似于歷史神話的成因和邏輯:在虛擬與事實、主觀與 客觀的內部關系的結構中再生產(chǎn)出超越對簡單真實的追求,而尋找到另外一種真實――“詩性邏輯”(poetic logic)。換言之,文本表述一旦脫離了作者就具有了經(jīng)久性,從而成為“事實”(fact)之后的“真實”(reality)。
三、“裝飾之美”:一種民族志范式的困惑
列維-斯特勞斯在《憂郁的熱帶》中曾對旅行中所觀察現(xiàn)象的復雜性表示困惑:“我所做的正是一個空間考古學家的本分工作,鍥而不舍地要從殘片遺物中去重現(xiàn)早已不存在的地方色彩,不過這種工作是徒勞無功的……有這種認識以后,幻想便開始一步一步地布下它的陷阱。我開始希望我能活在能夠做真正的旅行的時代里,能夠真正看到?jīng)]有被破壞、沒有被污染、沒有被弄亂的奇觀異景其本來面貌。”
列維-斯特勞斯試圖通過民族志研究對象的偶然性與變化性的事實存在,表達這樣的觀點:把客觀事實的“表象”記錄與描述當作這一學科的根本原則是一種對科學的誤識。在他看來,不斷變化的場域、時間的永恒變遷使人們對現(xiàn)象的描述變得蒼白無力,人類學家所要做的是在變化的表象中洞悉隱蔽在其后具有普世價值的“結構”。他在《憂郁的熱帶》中所引入的“旅行文化”對民族志范式的反思在“后現(xiàn)代”的今天顯得更為重要。利奧塔德用極簡單的話說:“我將后現(xiàn)代定義為對元敘事的懷疑態(tài)度。”具體地說:“后現(xiàn)代應當是這樣一種情形:在現(xiàn)代的范圍以內表象自身的形式使不可以表現(xiàn)之物實現(xiàn)出來;它本身也排斥優(yōu)美形式的愉悅,排斥趣味的同一,因為那種同一有可能集體來分享對難以企及的往事的緬懷;它往往尋求新的表現(xiàn),其目的并非是為了享有它們,倒是為了傳達一種強烈的不可表現(xiàn)之感。”20世紀60年代以降,隨著世界政治格局的改變,全球化經(jīng)濟與科技主義的發(fā)展,后現(xiàn)代主義演變?yōu)橐环N世界范圍的文化思潮。它對人類社會生產(chǎn)與生活方式的改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個異彩紛呈的世界是由圍繞在我們周圍的發(fā)達資本主義企業(yè)和自由的政治制度所開創(chuàng)的,現(xiàn)在它被稱為“后現(xiàn)代”。
“后現(xiàn)代”展現(xiàn)出以下三個方面的明顯特征,同時三者又具有互證性:(1)移動性/多樣性。“全球化”使得“現(xiàn)代性”敘事更加充分,不限于政治、經(jīng)濟領域,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也出現(xiàn)空前的“移動一流動”景象。學者根據(jù)“全球化的文化潮流”的變化情形,歸納出了五種“移動一流動”的圖景:族群圖景(ethnoscape),技術圖景(technoscape),財經(jīng)圖景(finanscape),觀念圖景(ideoscape)和媒體圖景(mediascape)。后現(xiàn)代社會的這種移動屬性使文化呈現(xiàn)出與傳統(tǒng)意義不同的多樣性。(2)擴容性/增值性。后現(xiàn)代主義的移動屬性通過大規(guī)模的群眾旅游活動使社會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擴容性”,即“社會內存”空前擴大,它必然導致表述上的另一個特征:“形象和象征的增殖與擴大。”民族志要在這一個特定的情境中去觀察對象的變化,并把它看成一個由“符號”(signs)和“象征”(symbols)構造的系統(tǒng)。民族志在當代旅游文化的情境中要面對所觀察對象從內容到形式上的“擴大化”。(3)遮蔽性/虛假性。伴隨著社會化再生產(chǎn)和技術主義的作用,民族志已經(jīng)從傳統(tǒng)的對“孤島社會”的觀察和了解進入到了復合性、互動性、多邊界社會;技術主義又加劇和強化了對文化的“裝飾”作用,致使民族者首先必須對對象的“真實性”進行甄別和確認。
當傳統(tǒng)的研究對象發(fā)生了變化,民族志的方法和范式勢必也要產(chǎn)生變革。今天的民族志者要如何面對“旅游文化”?如何觀察沒有固定空間、沒有確定的單位邊界?以什么方式獲取有效的資料?如何透過遮蔽性事物的表象去把握內在真實?這些都是民族志需要解決的難題。
當今的民族志挑戰(zhàn)包括:(1)事件的短暫延續(xù)性和參與者的即時參與性。這使得哪怕是最勤勉的人類學家也只能進行有限的田野調查。考慮到研究瞬間性的局限,人類學者對大量有效數(shù)據(jù)進行采集的惟一方法就是無數(shù)次的重復觀察和詢問成百上千的移動者,但是這種方法必然會采集到大量的沒有研究深度的定量數(shù)據(jù)。被調查對象在特殊情境中的特定心理狀態(tài):包括精神高度集中的、陷入沉思的、注意力分散的、嚴肅認真的、心理狀態(tài)不穩(wěn)定的等。這些狀況必然會影響民族志者的工作,包括進行訪談、調查、填表、甚至觀察時的深度和效度。(2)被調查者在特定的情況下很難表現(xiàn)他們的真實心理狀況,或表現(xiàn)心理上的多變,導致調查出現(xiàn)不真實和混亂的狀況。(3)由于民族志者對事件的短暫參與,很難期待他們將參與者置于連續(xù)的生活背景下對其做出深度的解釋,致使民族志者無法貿(mào)然下結論。這意味著,以傳統(tǒng)的民族志方式對移動人群進行研究時受到了極大的限制。為了探索新的方法,人類學家們正在進行多方面的試驗。格拉伯恩(Graburn)教授曾經(jīng)采用一套組合方法對游客進行調查(包括一些人類學家或其他學科的學者采用民族志方式對世界上一些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游客類型的歸類),值得我們借鑒,具體情況見下表:
對文化人類學的看法范文第4篇
[關鍵詞]植物;思維;認知人類學;民族科學;民間分類
[作者]崔明昆,云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博士;楊雪吟,云南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云南大學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昆明,650092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8)02―0056―008
自人類誕生以來,植物就與人發(fā)生了密切的關系。人類在自身的發(fā)展過程中,人與植物的關系不僅表現(xiàn)在植物為人類提供了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的必需品,也表現(xiàn)在人類認識和利用植物的過程中,植物對人類的思維活動以及認知模式等方面的影響,并形成了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本文從認知人類學的視角出發(fā),探討了植物與土著民族思維之間的相互關系,展示了民間植物分類過程中土著民族豐富多彩的思維特點,并以此說明了土著民族思維的邏輯性。
一、“原始思維”之爭與認知人類學
(一)“原始思維”之爭的由來
“原始思維”長期以來一直是學術界感興趣問題。其實,人類學的誕生就與探討此類問題有關。被稱為人類學之父的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的《原始文化》問世就標志著學者們從人類學的角度研究這一問題。在此后的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西方人類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從對原始文化的簡單認識,目的在于收集“原始思維”或“土著思維”如同“西方兒童思維”模式的證據(jù)到認知人類學者對土著民族仔細的田野調查,獲取客觀真實第一手資料,并從土著民族的傳統(tǒng)知識中尋找生態(tài)智慧及其對文明社會的啟示和反思作用為止,轉變之巨大令人吃驚。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于法國學者列維一布留爾的《原始思維》一書。這是因為,書中到處充盈著“西方中心主義”和“白人優(yōu)越”的種族主義觀點。然而,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列維一布留爾研究“原始思維”的最初念頭竟然來自他讀了法文譯本的司馬遷《史記》之后,中國史書在他的眼中便是“原始人”神秘思維的模式標本,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當代的部分中國學者讀了中譯本的《原始思維》后又引用該書中的觀點去分析《史記》,形成了一種東方主義神話的闡釋循環(huán)。
《原始思維》把原始人或土著人的思維看成與文明人的思維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思維方式,把原始人的“成年思維”等同于文明人的“兒童思維”。列維一布留爾認為,原始思維的方式特征是神秘的和前邏輯的,可見,他在“原始思維”和“文明思維”之間劃定了一條巨大的鴻溝。對此,人類學家做出了回應,例如,馬凌諾夫斯基(Malinowski)認為,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的理性,都可以認識同樣的邏輯規(guī)則,而且所有的人都將這些規(guī)則應用到他們的日常事務中。再如,美國人類學家保爾?拉定(Paul Radin)認為原始人和我們文明人一樣,擁有發(fā)達的智力水平和驚人的智慧成果。他認為,甚至西方人引以自豪的哲學,其實也是從原始人那里發(fā)端的。他借鑒人類學廣泛的田野調查資料,從一些重要的哲學性命題人手,揭示了原始人關于世界觀、生命觀等思想對西方哲學范式普適性價值的影響。例如,關于“自我”(ego),過去西方人一向認為原始人沒有“自我”觀念。拉定以毛利人為例,說明了毛利人不僅有自我的觀念,而且其復雜深刻的程度比西方的有過之而無不及。而E.E埃文斯一普理查德則分析了列維一布留爾得出錯誤結論的原因所在:列維-布留爾的錯誤部分地要歸因于在他最初形成他的理論時,所掌握的材料的貧乏,也要歸因于他以犧牲世間性和事實為代價而在好奇與感覺之間所做的雙重選擇。
此外,在對具體事物的分類認知中也存在著“土著人是如何分類”的爭論。例如,一些學者在談到土著民族對動植物的分類命名時認為土著民族“用名字來稱呼的只是那些有用的或有害的東西”。@對此,法國著名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以大量的事實,尤其是美國學者康克林對菲律賓群島的哈努諾人的田野調查資料說明,土著人對動植物的認識并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有規(guī)律的可循的。
由此可見,關于“原始思維”的爭論,從一開始就和“民族中心主義”以及“文化相對論”聯(lián)系在一起。隨著認知人類學的研究進展,作為思維方式認知論的“相對論”觀點越來越得到人類學家的認同。
(二)認知人類學――研究“土著人是如何思維”的科學方法論
結構功能人類學把文化看成制度,象征人類學把文化看成符號,而認知人類學則把文化看成知識,即研究對象的本土知識。認知人類學是研究隱藏在文字、故事、文化遺物等中的文化知識的學科。認知人類學家所要了解的是:作為群體的人們是如何理解和組織周圍世界中的物質現(xiàn)象、事件和經(jīng)驗的,其中包括從具體的客觀事物,如對野生動植物的分類到抽象事件如對正義的理解。
作為一門具有專門理論和研究方法的人類學分支學科――_認知人類學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美國耶魯大學的“民族科學”。民族科學在許多方面可以說是對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前人類學界占統(tǒng)治地位的民族學研究方法的一種反叛。傳統(tǒng)的民族志強調,為了對土著民的物質或精神層面的文化進行仔細的研究,人類學者要堅持實地調查。然而,當越來越多的學者走進田野后人們卻發(fā)現(xiàn),對同一田野點不同的時間進行重復調查后所得到的結果并不總是一致,而這又不能用時間的差異所引起的文化變異來加以解釋。這些前后相矛盾的民族志引發(fā)了這樣一個問題:民族志的可信程度究竟有多高?
矛盾的沖突源于雷德非爾德(Robert Redfield)與劉易思(Lewis)之間于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一場爭論。雷德非爾德曾經(jīng)在墨西哥的一個名叫特泊澤蘭的村寨中做過田野調查,并于1930年發(fā)表了關于當?shù)厝说难芯繄蟾妗:髞恚瑒⒁姿茧S一個調查隊重訪該地,并于1951年公布了他們的研究結果。雷德非爾德報告中描繪的是浸染了宗教和家族價值的村社圖景,協(xié)調與和合作是村社的規(guī)范。劉易思的圖景則相反,該村莊是被敵對情緒、嫉妒和競爭攪得四分五裂的村社,自我利益甚至壓倒親屬關系的聯(lián)結。由于前后兩次的研究結果差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無法用時間的差異來加以解釋。為此,民族志的真實性成了當時文化人類學界爭論的焦點。
經(jīng)過爭論,人們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的民族志存在一個重大的缺陷,即忽視了研究者自身文化因素的干擾。因為研究者往往根據(jù)自己的文化觀來設計調查方案和分析調查資料,這樣就難免使所撰寫的民族志存在一定的偏見。為了消除傳統(tǒng)民族志方法中存在的缺陷,20世紀50年代中期,一些人類學
家嘗試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民族文化,他們把自己的田野調查點看成自然科學的實驗室、把田野調查看成科學實驗,這就是所謂的“新民族志”(new ethnography)或民族科學。民族科學的出現(xiàn),標志著認知人類學的誕生。
傳統(tǒng)民族志的科學性和真實性問題由于應用了民族科學的研究方法首次得到解決。“民族科學”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美國人類學家古德納夫(Ward H.Goodenough)首先提出了作為民族科學理論基礎的文化概念,認為“所謂某個社會的文化,就是其成員明確認識的,相互關聯(lián)的,為進行解釋而形成的各種各樣的模式”。換句話說,文化就是桌個社會的分類體系。由于深受薩皮爾一沃爾夫假設,即文化模塑著民族思維的假設的影響,并采用雅各布森的結構語言學的方法,認知人類學試圖探究每個民族的分類體系,因而早期的認知人類學又稱為“民間分類學”(folk taxonomy)。從研究視角或研究者的立場來看,認知人類學借用派克(K.L.Pike)語言學中的兩個概念,即etic(源于phonetic,語音)和emic(源于phonemic,音位),來區(qū)分兩種研究立場。簡而言之,eric(客位)立場就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場來看待所研究的文化;emic(主位)立場則是站在局內人的立場對待所研究的文化。因此,認知人類學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分析的方法。
美國人類學家對民族科學的建立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作為民族科學的重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斯特蒂文特在其《民族科學研究》一文中對民族科學的性質和研究方法等進行了論述。他講到,雖然新民族志并沒有貶低其他民族志的意思,但“民族科學”這一名稱的使用還是令人遺憾的,因為它能使人們認為,除了民間分類和民間分類學是科學以外,其它的民族志都不是科學。然而,作者還是高度評價了民族科學,認為民族科學的研究方法有望提升整個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水準,民族科學提高了民族志的可信度、真實性和廣泛性。民族科學就是要建立一種研究某一社會對其物質和社會領域分類的方法。斯特蒂文特還列舉了作為方法論的民族科學方法之特征:主位法和客位法研究、研究領域、詞類變化與術語系統(tǒng)、成分分析、分類學及其研究程序等。作為語言學和人類學家的弗雷克主要從事土著民對環(huán)境世界的分類和認知研究,曾長期在菲律賓對不同文化的民族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田野調查,建立了一套獨特而完整的調查研究方法,進而成為了民族科學研究的先驅。弗雷克同時也強調,民族志研究者“應該努力根據(jù)他的研究對象的觀念系統(tǒng)來定義客觀物體”。他對歷史上研究土著民族是如何思維的民族志表示出了不滿,認為這不是進行真正的認知過程的調查研究,而是在收集“原始思維”(primitive thinking)的證據(jù)。他主張,認知人類學的研究應該與親屬關系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上的嚴格性相匹配,并最終形成一套了解土著民族對世界的理解之方法。對民族科學做出重要貢獻的還有美國耶魯大學著名人類學家康克林,其主要從事土著民族的親屬制度、顏色以及生物等的認知研究。《哈努諾人的顏色分類》是民族科學對顏色認知研究的開山之作,為人類學家開展顏色研究樹立了榜樣。其研究發(fā)現(xiàn),哈努諾人使用兩種不同的方法或者層次來區(qū)分顏色。第一層次是關于顏色的一般分類,這一層次的顏色具有明顯的對立性,它包括了四種固定的顏色:黑色、白色、紅色和綠色。第二層次包括上百種的特殊顏色,這一層次中的一些顏色會有交叉重疊(例如金黃色和橙色)。所有第二層次的顏色都被包含在了第一層次之中。日常生活中人們主要使用第一層次的顏色,只有當特別需要時才會使用第二層次的顏色術語。康克林的這一研究成果揭示了不同環(huán)境條件下人們認知上的多樣性。
柏林(B.Berlin)是美國新一代的民族科學研究者的代表,主要致力于民間分類與認知的研究,對顏色的認知也具有較出色的研究。其代表之作《基本的顏色詞:其普遍性與演化》對人學界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通過對一百多種語言的顏色詞后發(fā)現(xiàn),盡管各種語言的顏色詞分界不同,但是,人們對中心色的判斷是一致的,存在如下蘊含模式:
白/黑紅綠/黃藍褐
也就是說,任何語言,如果只有兩個顏色詞范疇,必然是白和黑;如果有三個,第三個范疇必然是紅。如此類推,如果有七個顏色范疇,第七個就是褐色。反過來,也就是說,如果某語言存在褐色范疇,則必然同時存在排列在它前面的其他六種顏色范疇。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關于顏色詞的普遍的認知規(guī)律,我們可以用它來解釋任何語言的顏色系統(tǒng)。
20世紀60-70年代,認知人類學在理論和方法上都發(fā)生了轉變。語言學的分析方法繼續(xù)提供理解和接近土著民的認知分類方法,然而,其重點不僅僅限于土著民對事物的分類及其關系的研究,也注意對分類的心理過程的研究。這一代的學者相信,存在著基于思維結構的心理過程,因此,所有的人類都具有普遍性。這些研究的視野不僅著重于對人的思想抽象系統(tǒng)的成分分析,而且擴展到對人的心理過程是如何與符號和觀念發(fā)生聯(lián)系等領域。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圖式理論成了認知人類學理解文化心理方面的主要手段。圖式理論的產(chǎn)生,可以說是認知人類學關注人與周圍環(huán)境互動的結果。圖式(schemas)是完全抽象了的實體(entities)和個人的無意識行為,是組織經(jīng)驗和理解社會成員所共享的世界模型,“它是一個由客體及其關系組成的框架”。圖式理論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心理實體。認知人類學者開始把人類學家概念化了的文化看成是部件(parts)而不是整體(wholes)。當然,這里所講的“部件”與傳統(tǒng)功能主義意義上的有所不同,它不再是構成整體的靜止實體,而是構成了認知的形成單位:特征、原始型、圖式、命題和認知分類等。文化可以通過分析這些單位,或稱文化片段(piece of culture)而得到解釋。當前的問題是:(1)文化片段事實上是否是共享的;(2)如果它們是共享的,那么共享的程度如何;(3)它們在個人與個人之間是如何分布的;(4)這些分布的片段是如何被內化的(internalized)。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事實上使得認知人類學的研究背離了人類學的主流而向心理學靠攏。
雖然德安德雷德(D'Andrade)聲稱,在20世紀80年代認知人類學在理解認知文化上就打破了對語言學的依賴,但是,人類學領域內有關認知研究的絕大部分成果仍是以語言學為基礎的。近期認知人類學中引用率很高的參考文獻之一:大衛(wèi)克羅內非爾德的《塑料眼鏡與教父》(Plastic Glasses and Church Father)仍是以語言學為基礎寫成的。上述事實說明,認知人類學的研究中,語言在理解和研究文化中仍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土著邏輯思維”的學科――民間植物分類學
民間植物分類(folk plant classification)是指科學分類以外的存在于民間中對植物進行分門別類的一種方法和過程。民族科學中,學者們對民間分類研究最透徹,成果最豐富的是民間植物分類學。這是因為,民族科學開始于人們對文化內涵事物的分類,而植物界作為人類生存的基礎,很自
然地成為了人們的分類對象,又由于植物界種類的多樣性,因此植物的民間分類在認知人類學的形成初期就成為民族科學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對象。也正是因為如此,有人把當時的民族科學又稱民間分類(folk classification)或民間分類學(folk taxonomy),更有甚者,甚至把認知人類學就稱為民間分類學。民族科學通過對民間植物分類的研究來揭示其分類方法、命名原理及其分類系統(tǒng),從而把握分類的認知意義,并以此說明土著民族的邏輯思維之特點。
康克林是人類學領域中,率先進行民間植物認知研究的學者。通過長期對菲律賓群島的哈努諾人的田野調查,于1954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哈努諾人與植物界的關系”。哈努諾人的植物學知識等方面的資料因被列維-斯特勞斯在《野性的思維》一書中的引用而著名。在哈努諾人的語言中,“有150多個名稱表示植物的各個部分和屬性。這些名稱為辨認植物和討論區(qū)分各類植物,而且還往往表明藥用和營養(yǎng)的重要特征的幾百種植物特性,提供了類目”。“哈努諾人的1625種植物類中的每一種都有專門的全名,它至少在一種組成成分中與一切其它名稱不同。植物的全名是由從一個到五個字詞單位組成的。最普通的形式是雙名組合”。康克林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民間生物分類,尤其是民間植物分類和命名的普遍原理的基礎。
作為人類學家的柏林,與生物學家雷文(Peter H,Raven)及布里德洛弗(Dennis E,Breedlove)合作,對民間生物分類學開展了跨學科研究。經(jīng)過長期對墨西哥南部和秘魯?shù)膹V大地區(qū)進行田野調查,尤其對墨西哥講瑪雅語的澤爾沱人的植物分類進行了詳細研究,他們在世界著名的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上先后發(fā)表了《民間分類學與生物分類》和《分類學的起源》兩篇重要文章。《民間分類學與生物分類》一文中,作者將澤爾沱人的民間植物分類和生物學(科學)分類進行了比較,劃分出了民間植物分類與生物分類的三種關系:粗分、細分和一一對應的關系。探討了這三種情況以及民間分類群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指出民間分類與科學分類存在可比性。在《分類學的起源》一文中,作者從民間生物分類的視角出發(fā),探討了生物(科學)分類學的起源,指出科學分類與民間分類的關系。在比較了墨西哥的澤爾沱人、菲律賓的哈努諾人、阿根廷的格阿拉尼人、美洲的那伐霍人等民間生物分類的基礎上,總結了民間生物分類的共同特征。通過對世界上民間生物分類的考察總結,得出了所有的民間植物分類,除了一些人群生活的特殊環(huán)境外,其分類的基本單位――“民間屬”的數(shù)量在250-800個屬的論斷(民間動物分類的情況也大致如此),這與列維-斯特勞斯的“大概在300-600之間,極少有例外”的估計基本吻合。他們所設計的民間植物分類方案被大多數(shù)的研究者所接受,并被證明對比較世界上不同地區(qū)、不同文化的民間植物分類是十分有用的。
美國人類學家布朗(Cecil H.Brown)是對民間植物分類中的重要分類依據(jù)――生活型(Lifeforms)的認知作了深入的研究,在《民間植物的生活型:它們的普遍性與演進》一文中。作者統(tǒng)計了世界上105種語言中有關植物生活型術語后,提出了民間植物生活型名稱的演化過程,即人類對植物生活型的認知順序,得出了如下的認知模式:
這就是說,在任何語言中,如果只有一種生活型的術語,那必然是“樹”(Tree);如果有二種生活型的名稱,第二個必然是“草”(Grass);如果還有其他的生活型名稱,就是藤本(Vine)或灌木(Bush),或是兩者都有。這就是關于民間植物生活型認知的普遍規(guī)律。
該文中,作者還討論了民間植物生活型術語的多少和社會的復雜程度以及植物多樣性的對應關系:“社會的復雜程度和民間植物生活型術語的多少具有緊密的關系。語言中只有兩種或少于兩種生活型術語的人群往往生活在缺乏復雜的政治整合和社會結構的小規(guī)模社會中,而語言中具有三種或三種以上生活型術語的人群則生活在技術復雜的社會中。生活型術語的豐富程度也與植物的物種多樣性密切相關,語言中缺少生活型術語的人群往往生活在植物多樣性貧乏的荒漠或極地苔原區(qū)。而語言中具有較多生活型術語的人群往往生活在植物多樣性豐富的溫帶林區(qū)或熱帶地區(qū)。”這一結論也有助于說明,人們對植物的認知思維主要與所的社會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有關,而和智力的高低并無必然的關聯(lián)。
民間植物生活型認知的普遍性也證明,現(xiàn)代人與“土著人”在對植物的認知及思維上是基本一致的。
隨著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生物多樣性減少速率的加快,使常規(guī)的科學分類方法在生物多樣性極為豐富地區(qū)的物種多樣性評估中顯出不足,因此,世界上的一些民族植物學家將民間生物分類系統(tǒng)應用在熱帶或敏感區(qū)域的物種多樣性快速評估中。對此,我國的民族植物學家也做出了有益的嘗試。他們以西雙版納的三個傣族村寨為調查對象,對當?shù)厝说闹参镎J知能力進行了探討,研究結果表明,傣族的植物識別程度與其年齡呈顯著正相關,中年以后識別能力趨于穩(wěn)定,識別率高達91%以上;通過與長期在西雙版納地區(qū)工作的野外植物分類學家相比較,研究者發(fā)現(xiàn)傣族土著民的植物識別率不低于分類學家,且所需時間比分類學家少。因而,該文作者認為,民間植物分類系統(tǒng)可以用于局部地區(qū)的物種多樣性快速評估。發(fā)表在保護生物學(conservation biology)上的《通過民間分類系統(tǒng)在熱帶雨林地區(qū)進行快速植物多樣性評估研究:以中國西雙版納個案研究為例》一文認為,土著民有著豐富的動植物知識,西雙版納傣族有著自己的植物分類系統(tǒng),通過對比研究表明,傣族的民間分類與科學分類在種的分類等級上有87.7%是一一對應的關系,這表明民間植物分類在一定區(qū)域內可以用于植物多樣性的快速評估,這有助于傳統(tǒng)知識和當?shù)厣锒鄻有缘谋Wo。以上研究結果是十分有趣的,它不但出乎許多植物學家的意外,也使許多人類學家感到驚奇,這也從另外一方面說明了民間植物分類與科學分類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也使得認知人類學中的“民間分類學”得以應用,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中發(fā)揮了作用。
本文作者通過長期的田野調查,研究了云南新平傣族的民間植物分類,闡釋了土著植物的分類與邏輯思維之間的關系。現(xiàn)簡要介紹其重要內容。
1、新平傣族植物的分類等級
對世界上一些植物民間分類的研究表明,民間分類的命名近乎完善地表明了民間分類的結構。植物民間分類等級也就是植物民間分類的認知結構。
分類等級是人們?yōu)榱颂幚矸诸悓ο蟮南嗨菩院拖喈愋运⑵饋淼牡燃壗Y構網(wǎng)。植物分類中,各種的分類群被安排在這些等級網(wǎng)絡中。研究表明,世界上許多的植物民間分類具有相似的分類等級,一般由4-5個等級組成。新平傣族的物分類等級由6個等級構成。
2、新平傣族民間分類與科學分類之間的比較
民間植物分類中,“屬”是基本的分類單位;而科學分類中,“種”是基本的分類單位。作者通過兩者之間的比較來看民問分類與科學分類在認知植物“種”上的異同。
根據(jù)民間屬和科學種的對應關系,可以將它們的關系劃分為三類:一類是民間屬與科學種一一對應的關系;第二類是1個民間屬包含了2個或2個以上科學種的關系(民間屬的粗分);第三類是1個科學種包含了2個或2個以上民間屬的關系(民間屬的細分)。
新平傣族410個民間屬中有354個屬與科學種是一一對應的,占到總屬數(shù)的86%;剩下的56屬中,有49屬屬于粗分,約占總屬數(shù)的12%;屬于細分的有7個屬,約占總屬數(shù)的2%。
民間屬與科學種高達86%的一一對應關系表明,新平傣族對“物種”的認知上與科學的概念較為接近。而民間屬的“粗分”和“細分”與植物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密切相關。文化上重要的植物往往采用“細分”,例如甘薯被細分為紅甘薯、自甘薯和黃甘薯。文化上不重要的植物往往采取“粗分”的處理辦法,絕大部分粗分的植物為草本植物,尤其是禾草類。當?shù)孛耖g分類中的“粗分”不失為處理豐富的植物多樣性,尤其是復雜類群的一種有效方式。
對文化人類學的看法范文第5篇
【關鍵詞】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
一、問題的來源與界定
當今,民族音樂學在世界范圍的影響越來越大,尤其是近年來,隨著一批又一批各國年輕學者投身到該學科中,為學科帶來了許多新的思想理念、方法和技術等等,更加推動了學科的迅猛發(fā)展。而在國內,民族音樂學或許還可以說是一門比較“新鮮”的學科,自上世紀70年代末上海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的羅傳開先生把“Ethnomusicology”轉譯成漢語“民族音樂學”后,這門學科常與同樣傾向于共時研究的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研究之間產(chǎn)生混淆,抑或常被誤解為僅僅是與民族音樂、傳統(tǒng)音樂研究有關的一門學科,一些學者甚至主張以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相關研究來代替西方民族音樂學,使之成為民族音樂學的“中國流派”的觀點。而實質上民族音樂學更多的是體現(xiàn)為一種學術觀念,無需在國籍以及研究對象上加以限定。
二、相關文獻列舉
20世紀西方民族音樂學的學說史大致可以分為50年代之前與50年代之后兩大階段。50年代之前,比較音樂學(一般被認為是民族音樂學的前身)的理論觀點經(jīng)一系列的批評后轉變到民族音樂學,其理論脈絡還是較為明晰的。50年代以來,民族音樂學在發(fā)展歷程中不斷受到各種人文思潮和眾多學科理論的影響,其學科研究領域、研究視角也在不斷地拓展,因此,對這一時期的民族音樂學發(fā)展脈絡難以很好的把握。民族音樂學發(fā)展迄今,已經(jīng)出版了不少經(jīng)典性的專著,其中就涉及到有關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的概念闡述,例如:艾倫?梅里亞姆(Alan?P?Merriam,1923――1980)的《音樂人類學》(1964年版,出版社:人民音樂)、《民族音樂學的研究》(1985年版,民族音樂學譯文集,出版社: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他認為:民族音樂學的目的和著眼點與其他學科的目的和著眼點并沒有什么明顯不同”,“它的特殊之處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認為有必要使人類學與音樂學這兩類資料相結合這一點上”,并強調“民族音樂學通常是由音樂和民族學這兩個不同的部分組成,可以認為它的主要任務并不是強調任何一方,而是采用雙方都考慮進去這種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為一體”,提出“對文化中的音樂的研究”;涅特爾在《什么叫民族音樂學》(1985年版,民族音樂學譯文集,出版社: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中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進行了分類,他認為這門學科“主要探討三類音樂,第一類有關無文字社會的音樂,第二類亞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種種音樂,即中國、日本、爪哇、巴厘島、西南亞、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語系諸國家(和地區(qū))的音樂文化,第三類是民俗音樂(folk music)可定義為,在上述亞洲高級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來傳承的音樂。”還有布魯諾?內特爾(Bruno Nettle,1930―)的《民族音樂學研究:31個問題與概念》(2004年版,出版社: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曼特爾?胡德(Mantle Hood,1918―2005)的《民族音樂學家》(1971年版),這些專著都是以具體的研究為實例來探討民族音樂學的理論和方法。國內學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民族音樂學的定義、范疇、理論以及方法也發(fā)表了多種不同的理解和觀點,但著作類比較少,大多為譯著,目前尚有的相關著作有杜亞雄的《民族音樂學概論》(出版社: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出版)。文獻類有:王靜怡的《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的歷史回顧與思考》(《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03期)其主要內容是:民族音樂學在民族學人類學的影響下,從開始的比較音樂學到后來的民族音樂學經(jīng)歷了學科誕生和發(fā)展的不斷完善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其研究對象不斷地發(fā)生變化,從開始的非歐音樂到全人類各民族的音樂、民俗音樂、大眾音樂等等。此文在各家各派的認識和現(xiàn)實研究的基礎上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作了思考和新的詮釋。湯亞汀的《西方民族音樂學思想發(fā)展的歷史軌跡》(《中國音樂學》,1999年第02期)主要按照歷史順序分析了民族音樂學學科思想轉變;汪平的《民族音樂學及其發(fā)展概況和研究范疇》(《寧夏大學學報》,2001年03期)認為民族音樂學是屬于音樂學范疇的一門理論性分支學科。民族音樂學是以世界各民族不同層次不同類型音樂為研究對象。這句話概括了它的研究對象和范圍,這是一個無比寬泛的范圍,人類包含著所有的種族,有人種的地方就存在著音樂,不管它是歐洲的、亞洲的、非洲的,不管它是傳統(tǒng)的、古典的、現(xiàn)代的,也不管它是屬于貴族的、平民的,是城市的、鄉(xiāng)村的、宮廷的,或所謂的陽春白雪,或所謂的下里巴人,都應該屬于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和研究的范圍;還有羅藝峰的《從普遍主義、相對主義到文化全元論――音樂人類學發(fā)展的“正、反、合”》(《貴州大學學報》,2002年02期);洛秦的《音樂人類學的歷史與發(fā)展綱要》(《音樂藝術》,2006年01期)等等,他們各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勾勒出了民族音樂學歷史發(fā)展的框架,并做出了對本門學科研究對象的看法,對筆者都有很大的啟發(fā)。
三、筆者對該問題的認識和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