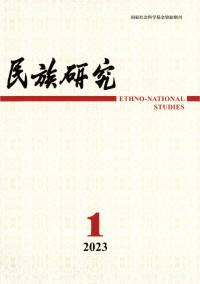民族形成與國家起源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民族形成與國家起源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論文關鍵詞]國家民族部落聯盟酋邦
[論文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是關于馬克思主義民族學和國家學說的重要文獻,在《起源》中,恩格斯通過對民族和國家形成過程的研究,指出了民族與國家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系。本文通過對《起源》的重讀,簡要分析了民族與國家的關系。
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通過對北美易洛魁氏族、希臘氏族和雅典國家的產生、羅馬氏族和國家以及德意志國家的形成的研究,并總結人類社會三次社會大分工中國家的產生,指出在國家產生的同時也產生了民族,國家和民族是在生產的社會大分工的出現,私有制的產生、家庭的變遷、氏族部落制度的變化的基礎上的必然產物。雖說國家和民族是兩個不同的事物,但二者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系。
正如恩格斯在《起源》第五章雅典國家的產生中所提到的那樣:“從有成文歷史的時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財產,這種情形正是和野蠻時代高級階段末期已經比較發達的商品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由于地產的買賣,由于農業和手工業、商業和航海業之間的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員,很快就都雜居起來;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區內,移來了這樣的居民,他們雖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不屬于這些團體,因而他們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是外人。在和平時期,每一個胞族和每一個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地區內而不屬于這個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不能參與這種管理。”“這就擾亂了氏族支付機關的正常活動,以致在”英雄時代就需要設法補救。于是實行了提修斯所規定的制度。……在雅典設立了中央管理機關,……以前由各部落獨立處理的一部分事務,被宣布為共同的事務,而移交給設在雅典的總議事會管轄了。由于這一點,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進了一步:相鄰的各部落的單純的聯盟,已經由這些部落融合為同意的民族所代替了。“一句話,氏族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社會一天天成長,越來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圍;……但在這時,國家已經不知不覺地發展起來了。”這表明那種單純的部落聯盟被民族和國家所代替是必然的,民族和國家是兩個共生性的社會共同體。
一、民族對國家的影響
當人類在其分化階段完成了不同民族的孕育之后,隨著人口的增長和自然資源的變化開始緩緩流動,而農業最早發生地區展示的良好生存環境驅使他們紛紛向這些地區匯集。于是,民族過程的聚合階段到來了。民族之間的交換、聯合和戰爭也造就了以階級對立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分層和軍事化的政治體制,為國家的產生創造了社會條件和組織基礎。國家起源于民族聚合,在于這種聚合帶來的社會沖突和為解決沖突引發的政治變革。民族聚合過程帶來了由民族碰撞激發起來的社會震蕩,也創造了平息這種震蕩的工具國家。
恩格斯在《起源》中提到:“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對內和對外都不得不更精密地團結其愛。親屬部落的聯盟,到處都成為必要的了;不久,各親屬部落的融合,從而各個部落領土融合為一個民族的共同領土,也成為必要的了。”從恩格斯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從部落融為民族的直接的原因是為戰爭。“鄰人的財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貪欲,在這些民族那里,獲得財富已成為主要的生活目的之一。……現在進行戰爭,則純粹是為了掠奪,戰爭成為經常的職業了。”
由于戰爭,“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對內和對外都不得不更緊密地團結起來。親屬部落的聯盟,到處都成為必要的了。”這種族體的聯合,恩格斯稱之為“部落聯盟”。部落聯盟有親屬部落的聯盟,也有非親屬部落的聯盟。它的特殊點在于各組成部落之間的平等聯盟關系。但實際上,除了部落聯盟之外,“酋邦”也是這種族體聯合的形式。酋邦的形成或經過部落之間的征服,或經過部落聯盟的演化。所以,不論酋邦還是部落聯盟,都是族體的聯合或增大。這種聯合或增大都是與這一時期社會分層的加劇同步而行的。這為社會沖突的發生增添了更大的可能,也為維持這種正在形成的社會提出了政治變革的需要。與之相對應的,是政治體制上的軍事化。恩格斯將其稱作軍事民主制,認為每個進入國家的文化民族都曾經歷過軍事民主制時代,如雅典的“荷馬時代”、羅馬的“王政時代”等。由于酋邦社會的發現,有的學者認為不宜再提“軍事民主制”。的確,恩格斯講到的軍事民主制是和部落聯盟對應的制度,這種制度都有人民大會、氏族首長議事會和軍事首長三種機構。而這些在酋邦那里只剩下后兩種或最后一種了,已沒有多少“民主”色彩。但無論如何軍事制度的痕跡十分濃厚,酋長也即是戰時的軍事首長,這和恩格斯講的部落聯盟沒有不同。部落聯盟和酋邦都可以成為國家的過渡形態。
前者因民主制度較濃,可以使過渡后的國家呈現共和的體制,如雅典和羅馬。“雅典是最純粹、最典型的形式:在這里,國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從氏族社會本身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只能夠產生的。在羅馬,氏族社會變成了閉關自守的貴族,貴族的四周則是人數眾多的、站在這一社會之外的、沒有權利只有義務的平民;平民的勝利炸毀了舊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廢墟上面建立了國家,而氏族貴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國家中了。”恩格斯進一步強調說:“雅典人國家的產生乃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為它的產生非常純粹,沒有任何外來的或內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為在這里,高度發展的國家形態,民主共和國,是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的;最后,因為我們是充分知道這個國家形成的一切重要的詳情的。”
而后者,因民主制度消退則可能走上專制了。恩格斯對德意志國家形成的敘述為此提供了具體事例:“我們知道,對被征服者的統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羅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須把所征服的地區加以組織。……因此,氏族制度的機關便必須轉化為國家機關,并且為時勢所迫,這種轉化還得非常迅速地進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軍事首長,被征服地區對內對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權力。于是軍事首長的力變為王權的時機便來了,這一轉變也終于實現了。”恩格斯在這里僅提到了軍事首長向王權的轉化,但卻是最具本質的轉化。因為只有王權才最深刻地體現著集權和強制,體現著國家和前國家政治機構的區別,其下屬政權機構的專門化也只有隨著王權的確立才能確立和擴展。
二、國家對民族的影響
人類的族體觀念,在原始社會前后,有過一個大的飛躍或變化。這種飛躍或變化經過了一些關系復雜的較長的過渡時期,但原始的血緣性的族體概念最終還是為地域性的超血緣族體概念所取代。例如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說的:“最初本是親屬部落的一些部落從分散狀態中又重新團結成永久的聯盟,這樣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而引起人類民族過程中這種飛躍或變化的主要原因正是人類社會政治組織形態的發展或者說是人類早期國家的形成。人類早期國家的形成促使文明民族的出現。
人類早期國家的形成之所以會導致新的族體觀念的出現,其原因是由于早期國家與原始社會中的血緣性的政治組織(如部落、部落聯盟等)不同,它具有控制和指導族源復雜的各原始社會民族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以及早期國家對于舊的血緣聯系的有意識的打破,而使在它控制下的居民按照地域和政治的原則重新進行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部落聯盟和酋邦。
由于部落聯盟與酋邦在政治組織性質上的差異,它們作為早期國家的前身,對于民族過程的影響也是不同的。
部落聯盟在政治上的民主與平等的特征,是以它仍然具有血緣團體的性質為基礎的。易洛魁人的部落聯盟,就是“五個血緣親屬部落以在部落的一切內部事務上完全平等和獨立為基礎”結成的“永世聯盟”。恩格斯強調指出:“這種血緣親屬關系是聯盟的真實基礎”。這就決定了在部落聯盟的范圍內,那種打破舊的血緣關系限制的新的、超血緣的族體概念,從整體上說還沒有形成,只有在部落聯盟轉化為國家之后,隨著國家政治職能作用的發揮,新的族體觀念才得以逐漸形成。這在歐洲早期的民族過程中表現得十分清楚。恩格斯在論述德意志人國家的形成時曾指出,羅馬帝國時期在羅馬國家的作用下,由于“到處都摧毀了古代的血族團體”,因而出現了一個“民族性缺乏”的時期,雖然“新民族的要素到處都已具備,……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備能夠把這些要素結成新民族的力量”,只有當德意志各原始民族“從羅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了新的國家”之后,才“養成了新的民族”。
然而,對于酋邦來說,新的族體觀念的形成過程,卻早在酋邦衍變為真正的早期國家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這主要是因為酋邦對于部落的結合并不嚴格地遵循相互間具有血緣聯系的原則,即酋邦并不像部落聯盟那樣以血緣親屬關系為其基礎。它形成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征服。酋邦在政治上所體現的專權或專制的性質正是這種征服的特征的反映和直接后果。酋邦的征服使不同血緣淵源的原始民族開始出現了融合為一種新型的、超血緣的族體的趨向。通過合并而形成文明民族的各原始民族,一般在地理上是毗近的,且在文化發展上處于相同或相近的水平,使用相同或類似的語言,并且在族源上是相對地同種的。如恩格斯所強調的“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對內和對外都不得不更精密地團結其愛。親屬部落的聯盟,到處都成為必要的了;不久,各親屬部落的融合,從而各個部落領土溶合為一個民族的共同領土,也成為必要的了。”“只有當結合在一個政府之下的諸部落融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時,……民族方始產生。”從中也可以看出,酋邦在吸收族源不同的居民方面具有很大的開放性與潛力。當然,相對地說,“同種”的居民是更易于被吸收的。但作為存在和形成的原則,酋邦并不拘泥于共同血緣關系的約束。這是歷史上經歷過酋邦時期的民族比從部落聯盟過渡到國家的民族能夠更早形成他們的新的族體關系的主要原因。
參考文獻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M],人民出版社,1972.1
[2]何潤,《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經典導讀》[M],中央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11
[3]謝維楊,《早期國家與民族形成的關系》[J],探索與爭鳴,1991.1
[4]王希恩,《國家起源與民族聚合》[J],民族研究,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