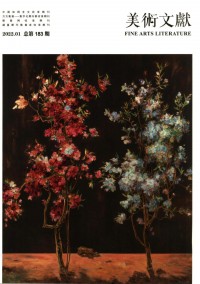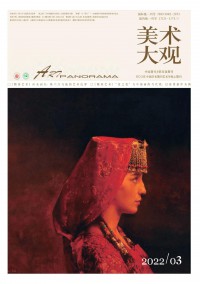繪畫語言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繪畫語言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繪畫語言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傳統的繼承個性創造墨守成規
關于傳統與創新似乎已是老生常談。對它們的把握許多人容易在不知不覺中走向偏頗,重視一方面而輕視另一方面。有的“藝術家”研究了一輩子的傳統也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頑固守舊。不愿直面現實生活的美術家,他的審美觀念永遠得不到更新的機會,只能停留在陳舊和保守的基礎上,他的藝術情趣因此也會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也就談不上創新了。也有的“畫家”對傳統的精華尚是一知半解,就忙著搶奪“觀念”,標榜“創新”,常是在建立空中樓閣,“墻上蘆葦根基淺”,經不起時間的推敲和考驗,這兩種人其實都走入了誤區。傳統是一定要繼承和發展的,任何事物都有其產生發展延續的過程,個性創造、風格的形成是我們對藝術追求的目標,但只一味地繼承或一味追求出新都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風格。
什么是傳統?傳統就是一種已經形成并對后世發生影響的東西。在藝術范圍內,可以說傳統是極為重要的,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傳統都在影響我們,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和研究它。繼承發揚有利于藝術發展的因素,清除掉阻礙藝術發展的因素,真正能吃透傳統的應當是精神非常強大的人,他既不畏懼于西方現代藝術觀念的涌入,也不非難各種對傳統的批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既吸收前人的養分,又不為之所困,始終以明智開放的心態去學習和創作,使我們的藝術更加飽滿充實。
中國繪畫從古典形態轉變為現代形式,始終沒有離開繼承傳統藝術的精神脈搏,只有這樣,才能創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感動人的作品。有人主張完全擺脫自然和文化傳統的束縛,也就是完全割裂傳統的繼承與開拓創造的關系。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過于夸張個性,這種個性一定是單薄和短命的。我們從西方繪畫史了解到:無論是野獸派、表現派還是立體派,不論其造型方法如何各異或者表現主觀感受的程度如何不同,他們最終都有一個明顯的繼承脈絡。
人類浩瀚的優秀文化成果就像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山花爛漫的原野,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去采摘,從而發展自己的藝術風格。回顧整個中外藝術史,有哪位大師不是踏著前人的肩頭向上登攀的?獨創性總是相對而言的,歷史上沒有絕對的、憑空的獨創性的東西。藝術史上所保留下來的,是一個個相互關聯的環節,這些環節織成一張大網,每一種藝術品在此都有一席之地,這張網就是傳統,沒有傳統也就沒有創新。傳統提供出一塊堅實的平臺,以便使藝術家向上跳躍,跳躍的結果構成另一高度,又成為下一跳躍的基礎。我們判斷一件作品是否有創造,也是基于傳統框架下決定的。
我們更應認識到,開拓創造是藝術傳統得以發展的動力,只一味墨守成規那是對傳統作無意義的重復,更難言發展了。傅抱石先生曾說過:“時代變了,筆墨不得不變”。其意義就在于他認識到了傳統的真正精神所在的同時,也認識到突破傳統的重要性。正因為他的這種認識,才使他創造出了“抱石皴”,事實上傳統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包容了諸多逆傳統而行的因素,才使傳統變得愈加豐厚。中國水墨在其發展過程中不也出現過如徐渭、石濤、林風眠這些不守成法的藝術家嗎?中國傳統的精神歷來是寬容創造鄙視守舊的。歷史證明,守成型的畫家多,開拓型的畫家少,但美術史總是由開拓型的畫家來書寫的。
創新與傳統的關系是藝術發展史上的一個永恒的命題。如何做到借古開今,既繼承優秀的傳統精神,又不囿于古人成法、陳法,這關系到藝術家的創造力、生命力以及個人努力探索等方面。人人皆知藝術要創新,從古至今的從藝者可謂眾矣,然而真正能做到創新者的并不多。這與社會人文環境、畫家個人秉賦等諸多因素都有關系,是一個綜合復雜的原因。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就應逐漸培養對事物的敏感判斷力和認知能力。如果這個時期不能使自己的感覺提升到一定水平,那么,藝術家的成年至老年很可能在其作品中顯現感覺上的遲鈍,表現出僵化保守。這就是有的畫家一生都在畫著同一個水平的作品的原因之一。有些大師如凡·高、高更雖然從事繪畫較晚,但在此前他們一定具備敏銳的感覺,所以后來才有天才的發現。又如齊白石先生六十歲后的變法并不僅僅是陳師曾等人的提醒,關鍵是他具有敏感的藝術神經從而形成超常的創造力。一個藝術家如發展到高層次的感覺和感情的升華階段,他可以靠敏感的直覺發現常人不易覺察的自然和內心之間那無限的豐富感,其藝術作品自然會表現出獨到的新鮮感。:
在人類文化史上,尤其是藝術史上,每一次藝術形式、意識、審美經驗的嬗變都是一些具有“先鋒”性質的創新者開辟了一個新的空間。西方藝術史上從法國的浪漫主義、印象主義、后印象主義、野獸派、立體主義、抽象主義均產生于對陳舊的藝術形式的揚棄。藝術作品的創作沒有開拓、沒有創新,作品的價值就會降低。藝術的開拓與繼承并不矛盾,它們相輔相成,關鍵在于你的認識、你的選擇。學習過程不僅是技藝的提高,而是藝術品位、藝術素質的培養。這樣就有了一個高度,我們盡可以在這個高度上再向上攀登。
參考文獻:
[1]鮑詩度.西方現代派美術.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
繪畫語言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作為表現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的諾爾德,其繪畫作品繼承了北歐傳統繪畫中的宗教意味和悲劇色彩。他繪畫中的宗教意味來自于他對宗教題材的直接選擇及表現性繪畫語言的運用,他的作品準確反映了時代的特征。他的繪畫無論從內在精神上還是外在語言上,都具有現代性。
埃米爾·諾爾德1867年出身于德國北部的一個農民家庭,17歲進人費倫斯堡的一家雕刻學校學習木雕,后來又在一家工藝美術學院短暫學習。32歲才有機會進人巴黎朱利安美術學院深造,從此走上藝術創作的道路。1906年,諾爾德參加德國表現主義社團“橋社”,成為“橋社”最重要的成員之一。但諾爾德性格孤僻,行事獨立,與橋社其他成員的激進表現格格不人,一年多以后又退出了該社團。1913年,諾爾德參加了南太平洋的一支科學考察隊,到俄國、中國、朝鮮、日本旅行,并留在南太平洋作畫數月。1956年卒。
諾爾德是20世紀初德國表現主義繪畫的代表人物,是“橋社”最有才華的成員之一。他的作品構圖飽滿,畫面簡潔,造型夸張,色彩強烈,筆觸狂放,作品中流露出強烈的宗教意味,或悲憫,或迷狂,或低沉,或激昂,將當時北歐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和普遍蔓延的世紀末情緒渲染得淋漓盡致。
一、何謂繪畫中的宗教意味
人類最早的藝術基本都與宗教有關。歐洲藝術在文藝復興之前,幾乎都是以宗教人物或宗教故事為繪畫和雕刻藝術創作的題材,藝術家通過藝術手段傳播宗教教義,為當時的教會服務。站在任何一件中世紀繪畫或雕刻的面前,立刻能夠感受到那種強烈的宗教神秘氣氛和宗教情感。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以宗教故事或人物為題材的藝術作品依然占有很大部分。直到17世紀以后,宗教題材的繪畫才漸漸被現實題材所代替。但是,后來的一些藝術家,尤其是那些性格內向的,喜歡沉思冥想的藝術家,依舊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作品中表達出宗教式的情感和意味。這種情感以動、靜兩種形式表現出來,一種是教徒式的宗教迷狂,表現為對某些事物的極端熱情或癡迷;另一種則為沉思冥想,悲天憫人的悲槍感受或超自然的心理體驗,這種情緒來自于藝術家內心的壓抑、痛苦,想尋找一種心理平靜或精神寄托。這兩種情感反映在繪畫當中,我們稱之為宗教情感或意味。
北歐的傳統繪畫中,自中世紀起就開始有了一種表達悲劇感和神秘體驗的傾向。從文藝復興的丟勒、格呂內瓦爾德,到19世紀的佛里德里希、布萊克,及后來的凡高、蒙克、恩索爾、霍德勒,直到諾爾德,他們的作品當中始終貫穿著悲劇色彩。不同的只是有些畫家采用內斂的、細膩的、沉穩的藝術表現手法,如弗里德里希的風景畫,多數則采用激昂外露,狂放不羈的表現手法,如凡高、蒙克、諾爾德等人的作品。20世紀初的表現主義畫家們,繼續開掘德國藝術中的悲劇意識,這種悲劇意識一度被稱為德意志民族的特征。藝術家們在對當時現狀不滿或不解的背后,試圖去尋找一種能表達現代人內心世界的藝術手法,那就是肆意的表現主義手法,諾爾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不懈探索者。
二、諾爾德繪畫中宗教意味的體現
1.選擇宗教題材表達宗教情感
諾爾德于1909年創作的作品《最后的晚餐》是其早期的代表作。這幅畫直接選材宗教故事,這是一個曾為眾多古典藝術家描繪過的不朽經典題材,最著名的是達芬奇的同名作。而諾爾德的這幅作品與古典大師常用的細膩寫實的手法含蓄地描繪這一宗教故事不同,他用極為夸張的表現主義手法來表現。諾爾德將基督與其門徒的形象無限放大,直到擠滿整個畫面,基督和眾門徒的臉上滿是憂郁與絕望,用紅、黃兩種明亮的純色和暗黑綠色鋪滿畫面,強烈的色彩對比,加上以基督為中心的戲劇性聚光效果,渲染出濃郁的悲劇氣氛。
19世紀以后,直接選擇宗教題材的畫家不多見,而諾爾德卻將一個經典的宗教題材作為表現對象,這與畫家想要表達的情緒有關。聯系當時的社會現狀,戰爭的陰云籠罩下的德國,無望的悲觀和狂躁不安是人們的普遍情緒,遁人宗教的世界里,尋求精神的自我解救或許是最好的出路,諾爾德就這樣將宗教故事與現實生活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諾爾德通過描繪與宗教相關的事物,如基督、傳教士、古老的哥特式教堂,及自然景物,如風車、大海、荒野、夜晚的月光等,將人們帶人無垠的神秘時空中,引起種種神秘的宗教體驗。這些宗教事物和自然景物從德國19世紀浪漫主義風景畫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以描繪宗教事物和自然景物傳達宗教意味的傳統表現手法在諾爾德的作品中得到了繼承。
2.通過繪畫語言體現宗教精神
在《最后的晚餐》一畫的構圖中,諾爾德沒有采用達芬奇式的將眾多人物一字排開的構圖方式,置于一個有著強烈透視感的和空間感的畫面當中,而是將所有的人物無限放大,擠滿整個畫面,消除了深度空間和精確透視,巨大的張力似乎要沖破畫面,悲憤的情緒因此得到有效釋放。
同樣的構圖手法還反映在另一幅作品《傳教士》中。這幅畫除了中上懸掛的一幅原始面具外,三個人物幾乎占滿了畫面,一位傳教士正對著雙膝跪地背著嬰兒的部落女人宣講圣經,或是這位傳教士在傾聽女人的懺悔。原始面具、傳教士、部落女人的畫面內容,再加上頂天立地的構圖方式,原始和宗教的精神意味在這幅作品中得到了有效的體現。
夸張的造型是諾爾德繪畫宗教意味得以體現的另一途徑。《傳教士》一畫,象征宗教的傳教士雙手緊抱圣經于胸前,幾何方形的臉上張大的嘴巴露出滿嘴的牙齒,說明他正在滔滔不絕地宣講教義,虔誠的女教徒雙膝跪地呈“之”字形。人物造型采用
極其夸張的手法,傳教士好似方幾何石塊的堆砌,或是隨手撕紙粘貼而成的,雙目、嘴巴、牙齒和胡須隨意地勾畫而來,墻上的原始面具也是極盡夸張之意,惟有婦女和嬰孩的造型稍微嚴謹一些。夸張的造型手法將教士傳教這一宗教事件凸現在觀者眼前,觀者感受到了畫面當中傳達出的濃郁的宗教氣氛。
作為早期表現主義團體成員之一,諾爾德也擅長于運用色彩和筆觸表達情感。《最后的晚餐》、《圍著金牛犢的舞蹈》、《狂熱舞蹈的孩子們》等作品都是用色彩和筆觸表達強烈情感的典范。
《最后的晚餐》里,諾爾德使用了炙熱的色彩與狂亂的筆觸渲染出畫面的宗教氣氛。《圍著金牛犢的舞蹈》中強烈的黃色與紫色,加上筆觸的任意揮灑,表現出舞蹈者動感十足的瘋狂跳躍,反復旋轉,如醉如癡的癲狂狀態,將激越的情緒盡情流淌在畫布上。諾爾德曾從凡高、蒙克和恩索爾等表現主義先驅那里繼承了用色彩和筆觸表達情感的手法。與“橋社”其他成員不同的是,諾爾德更多地表現悲憫、傷感的情緒,這種悲憫的情感或情緒來自于畫家對自然世界及現實人生的深人感受,經過了長時間的沉思默想,是畫家獨特的心理體驗,具有超自然的精神所指。而“橋社”其他畫家,更多地描繪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城市人聲色犬馬、紙醉金迷的生活場景,喧鬧的背后是一顆顆無所寄托的游魂,而諾爾德卻自甘咀嚼苦果,心向上帝,靈魂有了依托,痛苦的心靈得到解救。所以,看諾爾德的畫,必然要經歷一次次心靈跌宕起伏,之后沉寂下來,去自我追問或思考,這就是諾爾德繪畫的精神力量。
三、諾爾德繪畫的現代性
繪畫語言論文范文第3篇
1研究內容
我們將所搜集到的13篇文章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評述,即評述社會文化理論在二語習得領域中的應用的書籍,共兩篇(牛瑞英,2007;張虹、王薔,2010)。第二類是介紹二語習得領域中的兩大派別:認知理論和社會文化理論,共兩篇(高一虹、周燕,2009;高瑛,2009)。第三類是社會文化理論中的相關理論和概念在二語習得領域中的應用,包括中介理論、最近發展區理論、支架理論、動態評價等,共九篇(張雪梅,2002;張艷紅,2008、2010;高艷,2008;韓寶成,2009;楊華堂,2006;張曉勤,2008;張國榮,2004;蓋淑華,2010)。下面,我們分別作分析。
1.1評述
牛瑞英對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合寫的《社會文化理論和第二語言發展的起源》一書做了詳細的述介。認為該書全面、系統、清晰地呈現了社會文化理論所涵蓋的主要內容及其在二語習得領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現狀,其出版標志著社會文化理論和社會文化的二語習得研究的成熟(牛瑞英,2007)。張虹和王薔對KarenE.Johnson的《第二語言教師教育—社會文化視角》一書的內容和結構體作了介紹,并對書中提出的語言教師教育領域中五個正處于變革的觀點做了解讀和評述。對我國語言教師教育理論與實踐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張虹,王薔,2010)。
1.2兩大派別
認知學習觀和社會文化學習觀是二語習得領域業已形成的兩大流派(文秋芳,2008)。梁文霞、朱立霞(2007)對近20年國外四大主流應用語言學期刊有關二語課堂文獻的研究表明:二語課堂研究主要采用認知取向(cognitiveorientation)和社會取向(sociologicalorientation)兩種視角。兩個派別孰是孰非、孰重孰輕,一直以來是許多研究者關注的焦點。高瑛(2009)對比分析了認知與社會文化視域下的課堂互動話語研究。認知視域下的研究主要以輸入、輸出及互動假說為理論依據,采用靜態微觀量化分析,聚焦個體與生生互動,關注話語及互動的功能和形式。社會文化視域下的研究主要以最近發展區與支架式幫助為依據,采用動態宏、微觀結合的質化分析,聚焦群體與師生互動,關注互動中的意義、形式及結構,強調語境(高瑛,2009)。高瑛認為理想的發展趨勢是二者的有機結合,這樣才能更好的推動課堂互動話語的研究,更有力地幫助學習者習得第二語言。高一虹、周燕(2009)認為兩個學派在批評和借鑒的對話中,形成了一定的交疊,主要體現在對學習者整體“人”的關注以及對于多元性、動態性的注重。但二者也存在互補關系。在實證研究中,前者多采用量的方法;后者多采用質的方法(高一虹、周燕,2009)。
1.3相關理論
1.3.1中介理論
教師話語是學生語言輸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對學生的輸出甚至整個二語學習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學生把在課堂上所獲得的陳述性知識轉化成程序性知識需要中介。而教師的中介作用就是根據學生的需要選擇最佳的作用形式幫助他們實現知識的內化。高艷(2008)指出教師在語言教學中要關注語言學習者,為其創造有利于主動建構與發展的語言環境,幫助他們把在課堂環境下所獲得的內容,通過意義建構轉化成為真正的知識。教師用語言作為中介工具幫助學習者,而學習者用它來理解和內化新的知識,通過內化獲得個人認知和語言發展(高艷,2008)。楊華堂(2006)調查了高校英語教師和學生對教師中介作用的看法及教師中介作用在課堂上的發揮情況。結果顯示,教師的實踐和學生的理想之間存在較大差異與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他提出建議:一要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二讓學生有勝任感;三教學生用正確的策略學習;四促進學生的社會發展;
1.3.2支架理論
“支架”理論由新韋伯斯基派的學者如魯納(Bruner)、伍德(Wood)和麥瑟(Mercer)等人提出。旨在通過有效的教師-學習者互動形式,幫助學習者完成其自己無法獨立完成的任務。張國榮(2004)和張曉勤(2010)分別把“支架”理論運用到大學英語寫作和閱讀中,通過實驗最后都證實了“支架”理論應用于英語教學有以下幾點好處:一實現以“學生為中心”的現代教學理念;二充分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三充分挖掘學生的潛能;四減輕教師負擔,提高教學效果(張國榮,2004;張曉勤,2010)。蓋淑華(2010)將“支架式”教學法應用到詞塊教學中,探討二語詞塊習得能力及其與語言能力的關系。結果發現學生的詞塊習得能力得到顯著提高,同時,其綜合語言能力也有顯著進步;但詞塊能力對語言能力的各個方面的影響并不均衡,其中,對寫作能力的提高起著更為直接的作用(蓋淑華,2010)。張雪梅(2002)從“支架”理論出發,通過探討學習者會話的特征提出教師在設計課堂教學任務時可參考的有利于學習者會話的因素:一學習者會話的目的要清楚明了;二學習者會話的復雜性與難度應適中;三學習者會話設計應考慮學習者因素;四學習者會話中參與者角色應明確(張雪梅,2002)。
1.3.3動態評估
動態評估(DA,dynamicassessment)立足于智力的發展觀,跨越多個時間點觀察評估學生的進步與改變情況,了解學生動態認知歷程、學習遷移與認知能力變化的特點和潛能。“過程取向”和“教學介入與評估相結合”是其最鮮明的特點,同時它突出社會文化、非智力因素等對個體潛能的影響。張艷紅(2008)借鑒Lantolf的介入式動態評估(interventionistDA)的程序性設計理念和Poehner的交互式動態評估(interactionistDA)中的交互思想,探索網絡環境下對大學英語寫作教學實施動態評估的可能性。實驗證明,動態評估在寫作過程中為學生適時提供了策略、資源和激勵等方面的有效幫助,既有利于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又充分體現了教師的指導作用,使師生及生生之間形成了良好的互動,極大地促進了學生英語寫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張艷紅又通過實驗建構了大學英語寫作教學的動態評價體系,提出應該根據學習者的需求和發展狀況來設計循序漸進的“支架式”教學“介入”形式。韓寶成(2009)從關注點、目的、過程、結果解釋及評價者角色等方面區分和對比動態評價與靜態評價,詳細分析了干預式動態評價和互動式動態評價的特點和異同,介紹動態評價在二語教育領域的相關研究,并指出測驗的信度和效度應從更多實證層面獲得支持才有說服力。
2存在問題
社會文化理論的這些相關論文增進了我們對該理論的了解,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同時,我們認為這些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還有待改進:
2.1研究涉及面窄。主要是社會文化理論在寫作、閱讀領域的應用,關于會話的很少,聽力和翻譯的沒有。社會文化理論在英語學習的聽、說、讀、寫、譯五方面沒有得到均衡研究。
2.2歷史研究(longitudinalstudy)不足。研究主要以橫斷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為主,歷時的追蹤性研究只有一例:張曉勤(2008)。橫斷研究雖然能幫助我們了解一定時間的內師生行為,但只有進行歷時研究,我們才能了解學生的語言水平、了解教師或學生某一行為長期出現會產生的效果或某一教學措施對學生的遠期效果。
2.3數據來源較單一。實證研究只采取了單一的觀察、錄像、錄音或訪談來收集數據。這樣只能收集到參與者的行為或語言,卻不能充分探究其內心世界和心理過程。因此,今后的研究可結合教師或學生的反思,輔助以內省(introspection)和回顧(retrospection)的方法來挖掘造成他們特定語言或行為的深層原因(Ellis,1990)。
繪畫語言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會話禮貌理論;中日電話會話;跨文化語言教學
一、引言
中國和日本雖同屬漢文化圈,但兩國在社會風俗、語言習慣等方面仍存在著很大差異。而這些差異在跨文化交際中成為造成文化沖突或誤解的主要因素。這就要求我們平時在教學中要透視兩國語言間的差異,了解兩國人民的語言習慣,從而可以有效地避免文化沖突及誤解的產生。在眾多言語行為中,筆者選取電話中的請求行為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請求行為本身就是一個容易傷害他人面子、造成他人不快的言語行為。而且,以電話的方式實施請求時,雙方均看不到對方的表情和動作,只能通過語言來傳遞信息,因而有利于我們研究語言本身的技巧及策略。本文從“禮貌”的視角對中日兩國電話中的請求言語行為的使用差異進行考察,為跨文化語言教學提供借鑒。在禮貌理論中,布朗與列文森的禮貌理論及宇佐美的DP理論頗具影響力,從而成為分析言語行為的有效手段之一。為了真實再現電話中的請求言語行為,本文中的語料均選自中日兩國的影視作品及書籍。
二、會話禮貌理論
“禮貌”本身是日常生活中一項具有道德意義的行為準則,是人們為了維護人際和諧所做出的種種努力。但本文涉及到的禮貌是一種語用學概念。早在20世紀,Brown和Levinson(1987,以下略稱B&L)提出了禮貌的定義。他們指出,“禮貌就是典型人(Model Person)為滿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種理。他們的禮貌概念本質上是策略性的,即通過采取某種語言策略達到給交際各方都留點面子的目的。”①根據B&L的理論,人們都有希望獲得他人的肯定或理解的積極面子,以及其行為不受他人干預妨礙的消極面子。而人們為了達到順利交流的目的就必須采取一些語言策略來避免或消除威脅面子的行為。B&L禮貌原則的提出對當時的禮貌現象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B&L的理論也有其局限性:B&L理論僅用于對單句、單個表述層面進行分析,而不能用于分析整個會話表述是否恰當。為了填補這一不足,日本著名語言學家宇佐美真有美(宇佐美まゆみ)提出了會話禮貌理論(Discourse Politeness Theory,以下略稱DP理論)。她提出研究語言不能只局限在單句或單個表述本身恰當與否,而應該縱觀整個會話表述過程,研究這個過程的“基本態”,即某段特定會話的連鎖模式(発話の連鎖のパターン)。以下筆者以中日電話會話為例進行說明。
三、中日電話會話的“基本態”
筆者通過研究得出了14個電話會話的連鎖模式類型,歸納如下。
表1:
筆者通過對71段中日電話會話的分析,分別得出這些連鎖模式類型的使用率,如表2所示。
表2:
根據DP理論,凡是使用率超過了50%的會話連鎖模式就可以認定為此會話的“基本態”。因此,從以上兩個表格就不難得出中日電話會話的“基本態”。
中國電話會話的“基本態”為: 「注意喚起「身分表明「挨拶「事情説明「依頼「追加説明「會話終了
日本電話會話的“基本態”為:
「注意喚起「身分表明「配慮「事情説明「依頼「追加説明「再び依頼「後話題の挿入「會話終了
四、對跨文化語言教學的啟示
以上我們通過分析得出了中日兩國電話會話的不同的“基本態”。中國電話會話的“基本態”顯示,中國人打電話時在表明身份和簡單的寒暄之后馬上進入主題、表明打電話的目的,而委托完事情以及進一步補充說明后就結束通話了。而日本電話會話的連鎖模式就相對復雜,在表明身份以后,日本人通常會顧慮到對方是否方便接電話而向對方進行確認,得到肯定回答后再繼續對話,而且日本人習慣委托事情后再一次拜托對方,隨后閑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然后再結束通話。
所以在日本電話會話的教學過程,單純教授電話會話相應的日文表述是不夠的。如果不對日本電話會話的“基本態”進行說明,讓學習者充分了解日本人打電話的語言習慣,而是讓學習者按中國人習慣的電話會話模式進行的話,很可能在以后與日本人的交流中給對方帶來唐突的感覺。同樣,在日本人學習中文的過程中也需要學習中國電話會話的基本模式,如果還是生搬硬套日本那一套的話,可能會讓作為聽者的中國人覺得啰嗦或另有深意。
通過簡單的電話會話我們可以看出,跨文化語言教學不能只局限在逐字逐句的研究之中,同時也要對場景會話的整個結構模式進行把握,了解不同文化中不同的語言習慣模式,才不至于在跨文化交際中產生誤會或摩擦,從而更好地進行跨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1] Thomas(トマス).[淺羽亮一監修].『語用論入門―話し手と聞き手の相互交渉が生み出す意味―.研究社,1998
[2] 宇佐美あゆみ.『談話のポライトネス.國立國語研究所,2001
[3] 宇佐美あゆみ.「対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言語問題.『國立國語研究書巻冊の報告書.凡人社,2001
[4] 小泉保.『入門語用論研究理論と応用.研究社,2001
[5] 小泉保.『言外の言語學-日本語語用論.三省堂,1990
[6] 小泉保.『言語學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大學書林出版,1995中國語:
[7] 何自然、陳新仁編著.《當代語用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
[8] 何兆熊.《新編語用學概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繪畫語言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 社會文化 學習風格 教學風格
外語學習者的語言學習風格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具有自身的文化特點。同時,第二語言的本族語教師的教學風格具有其自身的文化特點。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學習風格與外籍教師的教學風格往往會產生文化沖突,影響語言學習效果。如何協調風格的跨文化沖突是語言教師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文化的定義和屬性
“文化”的范疇涵蓋了人類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及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文化具有自身獨特性,不同的民族、國家、社會、人群都有特殊的文化。了解文化的定義和屬性,有助于理解第二語言學習者在跨文化學習中遭遇到的學、教風格沖突問題,以期更好地加以解決。
1.文化定義。19世紀以來,國外學界對文化的理解逐步脫離神學體系和自然主義的束縛,開始轉向科學的理解。這種轉向源自19世紀英國人類學家Edward Tylor對文化的解釋,他在《原始文化》一書中首次定義了“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一個復合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及人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其是第一位在科學意義上給文化下定義的學者。
國內外學者在此基礎上積極探討“文化定義”,綜合各家觀點,文化的定義具體如下:(1)文化是物質文化、制度和習俗文化、精神文化三個層次的總和;(2)文化由外顯的和內隱的行為模式構成,這種行為模式通過象征符號獲致和傳遞;(3)文化代表了人類群體的顯著成就,其核心部分是傳統的觀念和價值;(4)文化是歷史上所創造的生存方式;(5)文化是信念、價值觀和生活習慣的“系統認知”;(6)文化無所不包、無處不在,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基礎。
2.文化屬性。學者普遍認為文化具有如下屬性:(1)文化是可被后天傳授的。文化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親身實踐、口口相傳或者書面語言進行傳授。(2)文化是群體共享的。文化可被理想化地推定檳騁簧緇嶧蛉禾逅有成員的共享行為。(3)文化是動態的。文化隨著時間發展、時代更替而不斷演變、進步。(4)文化是各種要素相互關聯的統一體。文化的各個方面是相互連接的,觸動其中一處,其他部分就都會受到影響。(5)文化具有約束性。文化具有教化功能,能指導約束人們行為。(6)文化具有民族、種族中心和群體中心的特點。特定的民族、種族和人群在特定的環境下,長期在一起生產、學習和生活,逐步形成了思維模式、價值觀、交往方式、社會習俗。
文化是一個復合型概念,既抽象又具體。只有了解文化的具體定義和屬性,我們才能進一步了解不同社會文化間的差異,才能扎實地探討第二語言學習中的跨文化沖突現象。
二、語言學習風格和教學風格的定義和類別
“語言學習風格”是學習者用以感知學習環境,進行信息交互的穩定的認知、情感和心理特質,是學習者吸收、處理和儲存新信息、新技能的方式,也是學習者吸納和理解新信息的內在特點。學習風格會受到社會因素、文化因素、學習環境、社區背景和家庭背景等外部因素的影響(Reid,1987,1995)。
“語言教學風格”則是教師在自身學習風格的基礎上形成的教學模式的傾向性。教師的教學風格與其本人的學習風格具有一致的特點,是其學習風格的直接反映。
語言學習風格和教學風格可分為如下類型(按對應組別分類):
1.感知型―直覺型(Sensing and Intuitive)。感知型學習者/教學者傾向通過“感官”觀察和收集數據,喜歡具體的事實和細節,強調記憶,喜愛規則和標準的程序,不喜歡過于復雜的事物。直覺型學習者/教學者往往不重視細節,傾向通過“下意識”感知、記憶。這類主體往往更為抽象,富有想象力,處理概念和理論的能力更高。
2.視覺型―口頭型(Visual and Verbal)。視覺型學習者/學習者習慣以視覺方式接受或呈現信息。口頭型學習者/教學者則習慣口頭指導。
3.主動型―反思型(Active and Reflective)。主動性學習者/教學者具有強烈的實踐動機和傾向,他們喜愛動作實踐活動。反思性學習者/教學者喜愛充分思考的環境條件,思考更有助于他們的記憶。
4.連續型―整體型(Sequential and Global)。連續型學習者/教學者以單元的相互關聯性為基礎來進行語言的理解和指導,喜歡分解詞匯和句型,偏好結構化的教學。整體型學習者/教學者習慣在整體層次上理解學習材料,傾向利用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去理解材料。
5.歸納型―演繹型。在歸納型學習與教學中,主體傾向觀察現象,推理論證,總結原則。在演繹型學習與教學中,主體以原理、規則為基礎,推導現象的結果。
三、社會文化對語言學習風格和教學風格的影響
社會文化是人們形成價值觀和學習理念的主要環境。因此,語言學習者和教師的社會文化背景是形成其學習風格和教學風格的重要原因(Oxford,1992)。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社會文化因素對學習/教學風格的影響受到人們的關注。對于各種類型的學習風格/教學風格,研究者們發現,不同國籍和民族的社會成員有不同偏好,分析如下:
1.整體型和分析型風格。拉美人更傾向整體型風格,如預測、推測(從語境中猜測),他們總體屬于高度的場依賴主體。中國師生多為整體型主體,他們會努力在不同事件和事物之間尋求統一性。歐洲裔、美國人多具有清晰分析和低語境化的抽象風格,他們把觀點基于邏輯推理而非人際關系之上,以尋找差異,找出因果關系。
2.場依賴型和場獨立型風格。歐洲裔、美國人的場獨立風格高于非洲裔美國人、拉美人和亞洲人。對中國人和日本人而言,他們多具有場依賴和場獨立的雙重特征。中、日的社會文化允許這兩種風格的同時存在:一方面,中日師生會根據社會語境做出整體的認知聯系,具有場依賴風格。另一方面,中日師生在嚴謹態度的引導下,講求細節,這促成了他們的場獨立風格。
3.情感型和思考型風格。拉美學生多為情感導向,具有明顯的群體導向。同時,他們傾向公開表達情感,屬于情感沖動型。日本學生期待教師尊重他們的隱私,不善表達個人情感,傾向在分析思考的基礎上進行判斷。日本學生喜愛高度結構化的演繹方式,傾向不斷糾正細節上的失誤,具有分析型傾向。同時,日本人注重反思,追求細節的完善,盡量減少冒險行為。非洲裔美國人和土著美國人尤為傾向思考型風格,這與土著美國人對生存環境的反思及非洲裔美國人對自身身份認同的思考有關。
4.沖動型和反思型。拉美人具有一定的沖動型風格傾向,這與其外向型風格相關。日本學生則表現出更積極的反思型特征,他們追求準確性,但不愿冒險。日本人往往深思熟慮以得到正確的答案,但不適應猜測式的方法。土著美國人往往表現得反思性過強,他們自尊心強,但在嘗試新事物時顯得過于被動,害怕“丟臉”。
5.具體連續型與直覺隨意型。東亞文化與阿拉伯文化注重具體連續的學習風格。中國、日本、韓國和埃及的人群具有具體連續型的學習風格,他們經常利用重復、強記、計劃、分析、列提綱的方式進行學習。歐洲裔美國人多數為直覺隨意型,他們在抽象思維、想象力、理論性、智力性和原創性等方面表現得更好。土著美國人和非洲裔美國人總體偏向具體連續型學習方式。
6.封閉型和開放型風格。亞洲學生往往對教師有一定的依賴性。如韓國學生堅持教師的權威性,以教師意見為重點。日本學生渴望得到教師快速而經常性的糾正。阿拉伯學生往往以排他性的觀點對待正確與錯誤,界線較為分明。非洲裔美國人比土著美國人表現出更多的封閉性特點,而土著美國人則具有靈活性、開放性、多樣性和變化性,喜愛非結構化的課堂。
7.外向型和內向型風格。以阿拉伯語為母語的人群喜愛交際、健談,偏好以整體班級為基礎的外向型學習方式。西班牙學生也表現為外向風格,他們高度社會化,合作性強,熱衷實現社會目標,對他人的需求敏感,并渴望與教師形成密切的關系。非洲裔美人相對外向,喜愛社交學習,喜愛在群體中分享,喜愛有新意的事物。非洲裔美國人在群體交流時還喜愛非口頭語言,如眼神交流等。土著美國人也表現出外向特點,合作性強,但對外來者懷有戒心。相對而言,亞洲學生謹慎和內斂。如日本和韓國學生屬于內向型風格,他們不喜歡公開的身體接觸,也不愿意表明自己的觀點和情感,總是顯得安靜、靦腆。
8.視覺型和聽覺型風格。東亞學生傾向視覺型學習風格,其中,韓國學生的傾向度最高,遠高于美國學生。同時,中國和阿拉伯學生具有強烈的視覺傾向,中國學生同時具有較強的聽覺特點。但是日本學習者則最不擅長聽覺學習。
研究表明,不同社會文化的成員具有自身傾向的風格偏好。在第二語言學習中,學習者接觸的是迥然不同的語言和社會文化及教學風格迥然不同的外籍教師,他們必然產生不適應乃至詫異的感覺,形成跨文化的風格沖突。
四、語言學習風格和教學風格的沖突及解決之道
根據相關研究和筆者的觀察實踐,第二語言學習者在課堂上往往不適應外籍教師的教學風格,他們的學習風格和教學風格在文化差異的背景下經常發生沖突,導致語言學習效果的削弱。比如,Oxford等人的研究就反映了這樣的跨文化沖突。該研究對中韓研究生、美國教師、美國研究生和中國教師進行了訪談。他們發現不同文化背景的師生具有不同的風格,導致跨文化的差異。中韓研究生對美國教師的整體型、開放型、直覺型和動手型風格感到壓力和焦慮,而美國研究生對中國教師的分析型和具體順序型風格不適應,這樣的“不適應”影響了學習效果。
據此,我們認為以第二語言為本族語的外籍教師,必須采取合適的教學措施,一方面,他們可以在教學風格上“契合”學生的學習風格,即充分了解學生的學習風格,調整和拓寬自己的教學風格,以適應學生風格,減少跨文化沖突,提高教學效率。另一方面,教師可以采取故意“不契合”的方式,促進學生在不適應的“教學風格”中調整自我,拓寬學習風格,提高跨文化適應性(呂玉蘭,2000),適應新環境,成為全面的學習者(All-round Learner)。無論是契合還是不契合的方式,第二語言教師都應該以學生為中心,從學習者的背景文化考慮學習者的心理和言語行為特點,為學習者創造理想的語言教學環境,增強他們的文化適應和第二語言學習效果。
參考文獻:
[1]Reid,J.M.The learning style preferences of ESL students.TESOL Quarterly,1987.21(1):87-111.
[2]Reid,J.M.Learning Styles in the ESL/EFL Classroom.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1995.
[3]Oxford,R.L.,Hollaway,M.E.,and Murillo,D.H.Language learning styles:research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teaching in the multicultural tertiary ESL/EFL classroom.System,1992.20(4):439-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