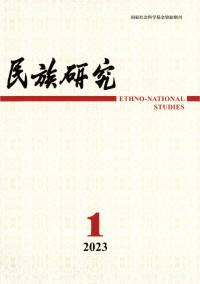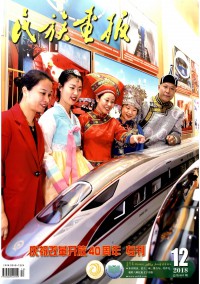民族考古學探索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民族考古學探索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民族考古學探索范文第1篇
我國東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馬橋文化等,都是這一時期命名的,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蘇秉琦先生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提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理論,對于我國考古學向縱深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略意義;對于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研究,無疑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區、系、類型”理論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據“區、系、類型”理論,蘇秉琦先生將我國群星璀璨的考古學文化歸納為六大區,“區、系、類型”中的“區”不僅空間大于考古學文化區,而且“區、系、類型”中“區”的層次也高于考古學文化區。蘇秉琦先生從全新的高度將“考古學文化區”的概念上升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區”,不僅為考古學建立了更加廣闊的時空框架,也為宏觀地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動態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蘇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的同時,還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一體”模式、從“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觀點到“古國、方國、帝國”的理論和“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為國家形成的三種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論,因此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理論實際上已成為通過考古學方法研究和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理論基礎③。考古學理論來源于考古學實踐,考古學理論應對學科研究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三十年過去了,當年蘇秉琦先生基于現有資料對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探索雖具有前瞻性,然這一理論在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實踐中也日漸顯現出理論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而出現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確。“區、系、類型”理論中出現了考古學文化的“區”、考古學文化的“系”和考古學文化的“類型”,蘇秉琦先生對“區、系、類型”的定義如下:“在準確劃分文化類型的基礎上,在較大的區域內以其文化內涵的異同歸納為若干文化系統。這里,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與原有的“考古學文化”、“考古學文化類型”等考古學專業名詞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義不同。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定義,“區、系、類型”中的“區是塊塊”,屬于空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區也同樣屬于空間范疇。在蘇秉琦先生劃分的六大區系中,“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即海岱地區;盡管蘇秉琦先生認為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屬另一個文化系統,實際上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可歸屬海岱地區的一個亞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則包含了太湖地區的“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寧鎮地區的“北陰陽營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學文化。
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劃分,“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大致相當于“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卻包含著“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陰陽營文化”和“薛家崗文化”的分布區。因此“區、系、類型”的“區”似乎既可等同于一個考古學文化區,又可包含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區。此外,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區”,或以省命名,如“陜甘晉”“、山東”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長江下游”“、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等。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學的基本標準④,而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中“區”的命名,既無統一的標準,又無規律可尋。“區、系、類型”中的“系是條條”,顯然屬于時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發展演進也同樣屬于時間范疇。根據蘇秉琦先生對大汶口文化發展演進為龍山文化和馬家浜文化發展演進為良渚文化的論述,“區、系、類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發展演進而不包括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文化分期屬于量變,而文化的發展演進則屬于質變,質變是由量變的積累而發生的突變。因此,“區、系、類型”中的“系”與文化分期、文化演進的相互關系的區分,“系”的時間概念與文化分期和文化演進的時間概念的區分,顯然存在著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在同一考古學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圍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異,往往又分為若干類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秦王寨類型”、“大司空村類型”和“西王村類型”等,而龍山文化則有“城子崖類型”和“兩城鎮類型”等。在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中,“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區、系、類型”中的“類型”與考古學文化的類型有著不同的概念。
“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與分支也同樣存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綜上所述,“區、系、類型”的“區”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區的“區”“,區、系、類型”的“類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類型”。考古學理論既須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又須符合形式邏輯的基本原理。一個學科中用同樣文字的專業名詞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著不同的定義,似乎有悖于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同一律。考古學理論應具有普遍性,應適用于不同時期的考古學研究。“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如僅適用于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區系的劃分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區。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蘇秉琦先生在“區、系、類型”中劃分的六大區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學文化空白區的情況下劃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區與下游地區。因此六大區系的劃分出現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東部和江淮中部地區在當時還是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區,還沒有龍虬莊、侯家寨、凌家灘、雙墩等遺址的發掘,還沒有龍虬莊文化、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據對古史傳說的研究,劃分了華夏、東夷和苗蠻民族集團的空間分布范圍。其中將渤海灣以西到錢塘江以北劃為東夷民族的分布空間⑤(圖一)。而蘇秉琦先生將我國東部沿海劃分為“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顯然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區,顯然強調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屬性而忽略了區系劃分的民族學屬性。“‘考古學文化’是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內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遺跡和遺物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應該屬于某一特定的社會集團的。由于這個社會集團有著共同的傳統,所以在它的遺跡和遺物上存在著這樣的共同性。
民族考古學探索范文第2篇
關鍵詞:20世紀;炎黃文化研究;回顧與思考
一、前言
早在先秦時期,即出現了“百家言黃帝”的局面,自漢代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擇其言優雅者”作《史記·五帝本紀》以來,中國上古史研究經歷了信古、疑古到考古這樣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
司馬遷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體系后,后世多認為信史,把黃帝時代看作中國上古史的開端,并把黃帝或炎黃二帝看作是華夏的人文始祖。一方面,這種民族與文化的認同感形成了極強的凝聚力,在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歷代添加甚或虛構而“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也使治上古史的學者們產生了許多困惑和懷疑。于是20世紀20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認為東周以前無信史,主張“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然而正如中國考古學的創始人李濟先生指出的,“這段思想十分混亂的時期也不是沒有產生任何社會價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國的考古學”。正是考古學的出現開辟了認識上古史的新途徑,才為解開中國史前史之謎找到了一把鑰匙。中國上古史的研究經歷了信古、疑古,最后走向考古。
從20世紀20年代中國考古學的誕生起,經過幾代考古學家們數十年的發掘和研究,獲得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考古資料,中國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在考古學家的鋤頭下逐漸顯現出來;人類的起源、農業的起源、文明的起源這些重大的學術問題也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就炎黃文化研究而言,“考古發現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傳說中‘五帝’活動的背景,為復原傳說時代的歷史提供了條件”。人們認識到,只有把文獻資料與考古資料乃至其他學科的資料結合起來,相互印證,才是重建中國上古史、研究炎黃文化的正確道路。
然而,“對古史的懷疑與對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紀中國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兩種思潮,這兩種思潮不但貫穿于二十世紀的始終而且將波及下個世紀。”因此,對中國上古史和炎黃文化的研究歷程的回顧與總結,是十分必要的,但實際上,筆者并沒有能力對數十年來炎黃文化的研究做一個全面的總結,只能從考古學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歷程做簡略的回顧與思考,企望能對今后的研究有所促進。
二、炎黃文化研究的回顧
(一)20世紀50年代以前
20世紀前期,考古發現對中國上古史研究的最大影響,是“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殷墟甲骨卜辭和敦煌漢簡等的發現開始,學者們就開始嘗試將地下材料與文獻材料相結合研究古史。特別是王國維利用甲骨材料撰寫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證實了《史記·殷本紀》記載殷商世系基本可靠,進而建立了“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的二重證據法。由殷墟甲骨發現而引發的殷墟考古發掘和一系列新發現,則進一步把殷商史建立在無可置疑的實物證據基礎之上。
20世紀20年代中國史前考古的一系列新發現,則把中國境內有人類的歷史追溯得更為古遠。1920年法國學者桑志華在甘肅慶陽首次發現了舊石器;1921年在北京周口店發現了猿人牙齒化石,同年在河南澠池發掘了仰韶村遺址進而確立了仰韶文化;1922年在內蒙古河套地區發現了“河套人”化石和石器;1928年在山東章丘縣龍山鎮發現了龍山文化。這些考古新發現、特別是北京猿人化石的發現,使學術界認識到,中國有^、類及其文化的歷史已很古遠了。
新的發現改變了上古史茫昧無稽的疑古觀點,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利用考古資料并結合古代文獻來探索中國古史。如徐中舒先生根據當時所發現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結合文獻記載的夏部族的活動地域,認為“從許多傳說較可靠的方面推測,仰韶似為虞夏民族遺址”。而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東、西對立分布似乎為當時頗為流行的“夷夏東西說”提供了依據。特別是徐旭生先生,20世紀30年代在陜西渭水流域調查時,曾發現了西安米家崖、寶雞姜城堡等新石器時代遺址,并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將傳說時代的部族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認為“炎帝氏族的發祥地在今陜西境內渭水上游一帶”,“黃帝氏族的發祥地大約在今陜西的北部”。
但新的考古發現對古史傳說時代的研究而言,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化石及石器的發現,雖然證明中國在距今數十萬年前的遠古時期就有人類生活、居住,但這些文化與傳說時代或炎黃時期相距太遠。新石器時代大約相當于傳說時期,“尤其是仰韶、龍山兩大系文化同傳說時代的古氏族的關系一定很密切。但關系的詳細情形如何及如何地變化,我們一直到現在還是幾乎毫無所知。我們也不敢捕風捉影地去附會,所以暫時也還不能談。”當時的考古學家們對炎黃文化的研究大都掙慎重的態度。
(二)20世紀50—80年代
20世紀50年代以來,大量的考古發現不斷拓展著人們的視野,學者們相信:“很古時代的傳說總有它歷史方面的素質,核心,并不是向壁虛造的。”一些考古學家們開始自覺地將考古發現和歷史文獻相結合來研究上古史。隨著考古發現確立了夏、商文化,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成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課題,而文明起源的探索又必然涉及到夏以前的“五帝”時期。因此考古學界關于炎黃文化的研究多與文明起源的研究相關聯。
20世紀50年代,石興邦先生主持發掘了著名的西安半坡遺址,使學術界對仰韶文化內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發現的由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的中間環節——廟底溝二期文化,初步建立了中原地區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時期的史前文化連續發展的體系。這些發現使學者們似乎看到了從仰韶文化經龍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一元發展軌跡,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原地區是中國文明發生地和演進的中心。這樣,一個祖先——黃帝,一條母親河——黃河,一個中心——中原地區就構成了“中原中心論”的主體認識,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而當時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自然被看成是中國文明的源頭,并與“黃帝文化”相關聯。如范文瀾先生認為:“仰韶文化所在地,當是黃帝族的文化遺址。”
1959年,徐旭生先生依據文獻“伊洛竭而夏亡”(《國語·周語上》)的記載,來到豫西尋找“夏墟”,并在偃師二里頭遺址找到了一種晚于龍山時代而早于商代的考古學文化。以后的多次調查、發掘表明,二里頭遺址是一處面積超過300萬平方米,由大
型宮殿式建筑和圍墻、高等級的墓葬、青銅器和玉器構成的復雜社會的遺存,它廣泛分布于文獻記載的夏人活動范圍——豫西和晉西南。大多數考古學家傾向于二里頭文化屬于文獻記載中的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應是夏代的都城。二里頭文化的發現,使得從仰韶時期,經龍山時代到夏商,形成了一個文化連續發展的鏈條,初步顯現了由史前文化到夏文明出現的軌跡,從而揭開了考古學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序幕。
20世紀60年代,隨著考古資料、特別是史前考古資料的增多,考古學家們已不滿足于證史或補史,而是尋求解決如何重建中國的上古史問題。李濟先生指出:“現代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不能僅限于找尋證據以重現中國過去的光輝,其更重要的責任,毋寧說是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下醞釀出的一些問題。這樣產生的問題屬于兩類,但兩者卻息息相關。其一是有關中華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為有關中國文明的性質及其成長。”之后,如何重建中國的上古史問題,成為史學界的一個重要學術課題。
20世紀70年代,在河南登封王城崗發現了一座距今4 000年以前的龍山時期古城址,安金槐先生提出的王城崗城址即文獻記載的“禹都陽城”的觀點,引起了學術界極大的關注和討論。這一發現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線索,客觀上把夏文化與史前文化聯系起來。不久,在山西襄汾陶寺找到了比“禹都陽城”更早的陶寺文化,先后發掘清理了上千座墓葬,其中大型墓隨葬有石馨、鼉鼓、彩繪龍盤、玉鉞、玉琮等分禮樂器,還出土了1件鈴形銅器。晉西南向有“夏墟”之稱,先秦文獻有“封唐叔于夏墟”(《左傳·定公四年》)的記載。因此,有學者認為活躍于“夏墟”,以龍為族徽、名號的陶寺類型文化,應是探索夏文化源頭的重要線索之一。也有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當為陶唐氏堯部落中心的所在。
(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
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業考古的新進展和新石器時代初期陶器的發現,使得中國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時間推進到距今10 000年前后;聚落考古在探索史前居民的社會組織結構及其演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環境考古則為探索文明起源的外部條件提供了許多新資料。在這些發現與研究的基礎上,文明起源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也不斷發展,促使相關學術研究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首先,考古學和文明起源理論有了較快的發展。1981年,蘇秉琦先生提出“區系類型理論”,把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分為6個區系。而這一文化時空分布格局表明,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有著多個區域演化中心,于是傳統的中國文明起源“一元論”或“中原中心論”受到了挑戰。蘇秉琦先生指出:“中國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它的發展并不是一條線貫徹始終,而是多條線互有交錯的網絡系統,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區系既相對穩定,又不是封閉的。通過區內外諸考古學文化的交匯、撞擊、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通過不斷地組合、重組,得到不斷更新,萌發出蓬勃生機,并最終殊途同歸,趨于融合。”張光直先生也指出:“中原文化只是這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它有它自己的歷史,也有它作為大系統中一部分的歷史,即影響其他文化與接受其他文化的歷史。”當然,在強調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的同時,并不能完全否認中原地區在文明起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嚴文明先生認為:“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處在各文化中心區的中間,易于接受周圍中文化區的先進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進下最先進入文明社會,從而成為這種多元一體結構的核心。”這樣,“多元一體”文明起源觀點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認識。
其次,文明與社會演進過程的研究受到普遍的重視,提出或借鑒了多種社會發展理論與模式。1983年,張光直先生首次將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塞維斯(elman serrice)的人類社會演進由游團一部落一酋邦一國家的4個階段構成的模式介紹到中國,并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階段進行了初步研究,認為龍山時代屬由平等社會向國家過渡的酋邦階段。之后,所謂的“酋邦理論”受到國內一部分學者的重視,并開展了相關的研究。1986年,蘇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國”的文明起源過程三階段模式,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鄉最初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古國則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嚴文明先生認為:依據相關文獻記述,“五帝時代是一個普遍筑城建國的時代,這恰恰與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相合”。中國古代把城叫做國,城外的鄉村叫野,包括城鄉的政治實體有時也叫邦。如果套用酋邦的說法,龍山時代似乎相當于酋邦階段,但“我主張先不要硬套,就用中國古代習用的名稱叫國。因為這時期的國剛剛從部落社會中脫胎出來,還保留濃厚的部落社會印記。為了跟后來比較成熟形態的國家相區別,可以稱為原始國家或古國,代表中國古代文明的黎明時期。”進而提出古國(龍山時代)一王國(夏商周三代)一帝國(秦至清)的文明起源與發展三階段模式。
再次,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前考古的新發現、特別是龍山時代大量的城址、銅器和陶文等發現,為中國文明的起源“多元一體”的理論提供了許多新證據。就炎黃文化研究而言,“考古發現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傳說中‘五帝’活動的背景,為復原傳說時代的歷史提供了條件。在黃河上游齊家文化出土了許多銅器,有銅錐、銅刀、銅鉆頭、銅鑿、銅環、空首斧、銅鏡等,這些銅器有鍛造,也有單范鑄造的。有學者認為,中原地區銅器的出現與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關系。黃河中下游地區發現有許多城址,其中在陶寺遺址新發現了陶寺文化是、中期城址,中期的大城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特別是在一件陶扁壺殘片上有朱書似“文”和“易”字的陶文。此外,在山東鄒平丁公遺址也發現—塊刻有11個字y的陶片。這些發現為探索文明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資料。在長江下游,發現有瑤山、反山等高規格的祭壇墓地和以莫角山巨型夯土臺基為中心的城址,面積達290萬平方米。在長江中游,發現面積達120萬平方米的湖北天門石家河城址,出土了數以千計的陶塑動物。嚴文明先生指出:“這個時代確實是處處閃耀著文明的火花,對于后世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這樣的時代自然會長期為人們所懷念,宜乎后人把黃帝推崇為人文始祖。”因此“把龍山時代同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相比照,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甚至有學者主張將這一時期稱為“五帝時代”,認為“惟有稱為五帝時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現中國古代的歷史實際和這一階段的時代本質”。
三、炎黃文化研究的思考
20世紀20年代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考古學發現與研究的進程,包括炎黃文化研究在內的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斷取得新的成果,推動這一課題研究不斷向更高、更深的層次發展,但我們還應看到,這一領域的研究也還存在著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首先,炎黃文化應屬中國上古史(或史前史)和
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內容。張豈之先生指出:“我們研究中國文化的源頭,研究先秦時期原創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國文明起源的大課題相聯系。”依據“多元一體”的理論,炎黃文化僅是史前諸多文化中的一支,盡管這一支文化在文明起源過程中可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炎黃文化本身的形成乃至文明的起源,應是多種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結果,故探索炎黃文化的同時,也要注意研究其他文化及與炎黃文化的關系研究。因此,研究炎黃文化應將其納入中國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體系之中,在“多元一體”的框架內,首先努力從考古學文化的內涵分析來探討傳說時代或“炎黃文化”的歷史面貌,探索炎黃文化的形成及基本特征,炎黃文化的發展直至文明的出現等。但目前,史學界仍有部分學者忽視“五帝”時期文化多元不平衡的發展過程,對古代傳說和記載又不加檢視地應用,熱衷用文獻附會考古發現或者用考古發現附會文獻,甚至直接將考古發現與古史傳說中某些人物或事件對號入座。這類研究顯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包括炎黃文化在內的中國上古史(或史前史)重建,應建立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基礎之上,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乃至現代科學技術的參與協作。早在20世紀60年代,李濟先生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中指出:“我們講現代人類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屬于人文科學的范圍;同時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學研究的題目”,并提出了上古史重建的材料范圍包括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和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紀載。蘇秉琦先生也指出:“一部史前史,既是人類社會發展史,文化史,又是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歷史,這種性質決定它必須是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成果,不僅需要吸收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成果,還要借助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許多自然科學或新技術手段。”但目前,多學科協作仍不甚理想,各個學科各自為戰的現象仍較普遍,特別是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合作尚需進一步加強。
四、結語
從上述回顧可以看出,從20世紀考古學產生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中國史前考古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已建立了較為清晰的史前文化時空分布框架。但其中也存在著一些需要進一步思考或探索的問題,文明起源和炎黃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遠。
民族考古學探索范文第3篇
夏文化問題是中國考古學中的重要課題。參加探討的學者之多,數量之多,都是其它考古學研究課題所不及的。然而,在這熱烈的外表背后,我們卻不能不看到,目前的夏文化研究在基本概念和定義上,在理論和方法上,在研究角度和重點上,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問題。由于夏文化定義的不準確,在推斷何者為夏文化時,研究者們所指的對象就不會完全一致,難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周密,在夏文化的討論中,各家的結論都無法使對方折服,認識的分歧自然難以消除;由于研究重點的偏頗,夏文化研究者爭論的中心主要是伊洛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中的夏和商的分界,從而忽略了一些本來應當首先加以討論的基本問題。有見于此,我們有必要對夏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探討,以求得某種程度上認識的一致,以利于今后夏文化問題研究的深入進行。
一、夏文化的概念和定義問題
夏文化的探討,它的概念問題是一個首當其沖的問題。夏文化是一個考古學文化的概念,還是一個人類學文化的概念,這是需要參加夏文化研討的學者首先明確的。多數研究者恐怕會認為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為考古學上的夏文化當然應當是考古學文化的概念。但是,事情并非這樣簡單。在一些夏文化研究者的論文中,他們所說的夏文化,年代不在夏積年的范圍中,地域也在夏王朝統治區域外,文化內涵也不是考古學文化遺存所表現的東西。這些研究者所論的夏文化與多數研究者所論的夏文化,其概念就不是一個。這是夏文化探討需要注意并加以區分的。
夏文化既然是一個需要探索的考古學文化,那么,作為一種考古學文化,它就至少應具有時間、地域和遺存特質這三方面的要素,需要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定義。夏鼐先生將夏文化定義為:“夏文化應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該定義包含了時間限度和文化族屬這兩個方面,而對空間范圍和社會性質卻未作說明。鄒衡先生則認為:夏文化的定義必須包括后兩方面的內容。按照鄒先生的意思,夏文化的完整定義應表述為:夏文化是在夏王朝統治時期、夏王朝所處地域內的有一組文獻記載中夏人禮器的青銅文化,在這種文化中應有宗廟、青銅禮器等反映夏王朝國家形態的遺存存在。
夏、鄒二位先生對于夏文化定義的闡述,代表了大多數夏文化研究者對于夏文化的看法。按照這種夏文化的定義,夏文化的起止時間也就是夏王朝的興亡時間,即上限為禹啟建國,下限為夏桀亡國。然而,一種考古學文化的時間界限決不會同一個王朝存在年代完全等同,它不會因一個王朝的建立而突然產生,也不會在舊王朝滅亡和新王朝建立那天突然中止。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產生、發展、繁盛、衰落乃至于滅亡的過程,夏文化如果是以歷史上建立了夏王朝的夏人為主體的文化遺存,它出現的時間就很可能在夏王朝建立以前,它的消亡也應當在夏王朝滅亡以后。用夏朝的存在年代來界定夏文化的時間范圍,這顯然是不妥當的。
還需要指出的是,夏文化在目前乃至于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它都只是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一個課題,它還不是一個實際確定了的考古學文化的命名。研究者可以提出證據來推論某種考古學文化可能屬于夏文化,但卻不宜按自己的觀點將該考古學文化命名為夏文化。用傳說時代或原始時代的族名或國名來命名考古學文化,很容易出現錯誤和產生誤解,應當盡量慎重。
二、探索夏文化的步驟和條件問題
夏文化是中國歷史上以夏人為主體的古族的遺存,而夏人遺存的文化特質又無疑是在夏人居統治地位的夏王朝統治時期和夏王朝統治地域內表現得最為突出。因此,探索夏文化應首先探索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這是不言而喻的。在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遺存尚未被確定以前,就試圖尋找夏王朝以前的夏文化遺存,追溯夏文化的源頭,提出所謂“先夏文化”問題,那是缺乏基礎的。至于試圖通過文獻記載的夏遺民和所謂夏禹后裔活動地域的遺存與夏王朝統治區域內的遺存的比較來反證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從末流向上逆推,這在夏文化已經衰落、文化特質不很明顯的情況下,其收效也不會理想的。
我們認為,要從考古遺存中確定夏文化,首先要從辨識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遺存人手;而要確認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則應當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夏王朝存在的年代范圍及地域范圍的基本確定;第二個條件是夏王朝地域范圍內及其相關周邊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及概差絕對年代框架的建立:第三個條件是有若干能與文獻記載的夏人禮制習俗和技藝水平相吻合的遺存發現。關于第一個條件,通過研究者們對歷史文獻材料的收集疏理,夏王朝存在于公元前2loo年至前1550年間的河南省中西部及山西省南部一帶,現在已基本可以肯定,這個條件已經具備。關于第二個條件,通過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從龍山時代至商代早期,在河南省大部和山西省南部,考古學文化的序列已環環緊扣,并有較多的’‘c測年數據可供參考:這個條件也已經滿足。至于第三個條件,目前的情況還不是那么令人滿意,雖然有大型城邑和宮室遺存的發現,但尚缺乏帶有較多歷史信息的遺存(諸如保存較好的大型墓葬、晶級較高的青銅禮器等)。這就使得在夏文化研究時,每每有內證不夠充分的感覺。努力尋找這一方面的材料,使得這一條件逐漸具備,是今后論證夏王朝時期的夏人遺存和最終確定夏文化的重要任務之一。
三、夏文化探索的途徑及方法問題
夏王朝時期夏文化的探索,經過十多年來的研究和爭論,目前探索的對象已主要集中到二里頭文化及其相關遺存上。這是由于二里頭文化在年代、分布地域和社會發展水平上與文獻記載的夏王朝的情況最為接近的緣故。然而,由于考古發現的能證明為夏人文化特征的遺存尚不夠充分,研究的角度和途徑尚比較單一,目前參加夏文化問題討論的諸方誰也拿不出有力的證據和有效的方法來說服對方。從近些年來夏文化研討的情況來看,研究者主要是通過這樣幾個方面來論證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
1,通過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岡文化各自內部及二者之間的文化面貌的發展變化程度的分析,來確定考古遺存的夏、商分界,進而確定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
2.通過考古材料反映的歷史信息,如宮殿和都邑的興廢所反映的社會政治變動,結合歷史文獻中夏商史跡和夏商都邑的情況,來確定夏、商分界,進而推定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
3.根據歷史文獻中夏人遷徙的傳說,通過夏王朝統治區域及所謂夏人遷徙所至地域的相關考古學文化因素的比較,從二者的文化分期與相對年代關系上去推定夏、商分界,進而確定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
民族考古學探索范文第4篇
章可樂古墓群考古發掘的重大學術意義,就如報告《序言》的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長劉慶柱研究員所說,它的墓葬群的時代序列、青銅文化特點、葬俗、總體的文化風貌、可供文物、考古、科技與民族史等各學科展開綜合研究的豐富資料,早已引起海內外人士的高度關注,不僅媒體紛紛追蹤報道,而且人選“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首屆“中國考古新發現學術報告會”。
這里,筆者要強調的另一層意義則是,貴州上古民族的文明史,它是以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和兩漢書有關“夜郎”的記載而聞名于世,但因后續史料缺失,夜郎王國又成了千古之謎,無論史家如何從古籍搜索都難揭開其神秘的面紗,今唯有依靠考古發掘才能使我們心目中的夜郎國面目日漸豐滿。眼下的《可樂報告》,就是戰國秦漢時期分布于黔西北的土著民族的數百座墓葬群的發掘收獲,它的發現與研究,無疑是夜郎時代考古取得重要突破的標志。先睹為快,筆者試將閱讀心得陳述如下與同好分享,不當之處,也敬請方家指正。
一、編寫體例的創新
首先,筆者認為該報告有一較好的編寫體例結構,《赫章可樂二年發掘報告》由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發行,該書為16開精裝本,有正文476頁,文后有彩色圖版75幅,黑色圖版12幅(定價420元)。全書分六編十數個章節,對發掘收獲作了分門別類的描述和分析概括。
應當說,考古學研究有其特有的專業語境和學術要求,這一點《可樂報告》與過去的考古大型報告沒有本質的區別。但報告者力求創新并竭力施惠于后學,于每編目下又特辟“發掘者說”一章節,其中披露了通俗易懂的專業心得介紹,目的是更好地能將所獲考古資料供同行和跨學科的研究者使用。此外,作者以“學術,天下之公器”為己任,還專辟“田野疏漏項清點”一節,其自我批判和嚴謹的科學態度,真可謂虛若懷谷,令人敬佩!這也是在過去的專業考古報告中所罕見的風范。
當然,就此而言,筆者也要指出其中的遺憾,那就是報告中敘述數十年的發掘探索的經歷過程,還是過于簡略。我們不能不指出,中國迄今為止,難見一部較完備的中國考古學史,有趣的考古探險歷程、曲折跌宕的驚世發現,都因當事人的離去而永遠塵封黃土,此因為是堆積如山的文物考古報告都略去文物背后的人與事,從而使考古僅僅是成為了少數學者的專利。事實上,學術史的總結,是每一門科學得以繼承發展的基本前提,它不僅是使前人的業績貢獻彪炳于史冊,使前人的優點缺憾為后人明鑒。更重要的是能使后繼之科學和真理得以光大發揚。從這一意義上說,讀了《可樂報告》的有關章節,它使我更容易聯想到李濟先生的《西陰村史前的遺存》、《安陽》等著作,有一種歸真返璞之感。的確,中國要多產生一些類似于英國學者伊文思《克里特發掘記》、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這樣雅俗共賞的作品,才有可能會產生公認的中國考古學史,要實現這一目標,看來還不能不從文物考古的調查、發掘報告的寫作入手。
第二點,筆者在此著重談一下《可樂報告》的科學文化價值。
二、《:可樂報告》的科學價值
可樂墓葬群有數百座,時間跨度從戰國早期延續到西漢時期,這近500年間,除了史籍不過幾千字的記載,基本上可說是貴州地區歷史的空白。《可樂報告》能提供的重要史實很多,最重要的是它初步確定了黔西地區戰國秦漢墓葬的歷史編年。因為此問題不能很好的解決,任何夜郎時代問題的研究都不免是空中樓閣。
《可樂報告》的年代分期手段,主要是采用地層學(如墓葬的打破與疊壓關系等)、器物類型學比較結合絕對年代測年數據作出分析判斷,因而其結論是科學的。它不僅有綜合性的分期論述,也有個別文物深入的類型學分期,如揭示柳葉形銅劍演變的時代序列就十分清晰(159頁),令人信服。美中不足的是因出土陶器還不算多,報告所揭示的考古學文化的發展演變面目還不夠十分豐滿,用圖表方式表述還稍有欠缺,而這一點恰好是命名一個新的考古學文化最有說服力的基點。因此,作者只好謹慎地說,可樂的發現要確定為一種新的考古文化的條件還不夠充分(6頁)。
《可樂報告》歷史編年的確立,意味著,夜郎時代前期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四至五世紀。其上限要早于《史記》的記載二百多年。
《可樂報告》最耐人尋味的章節是“發掘者說”,其中披露了以往報告多忽略的細節。如提醒讀者注意第二工區墓葬密集,打破關系極多令人吃驚。這很容易促使讀者作進一步的思考:這種現象或可能反映,當地居民的流動性大,過往流徙的古代族群可能不止一支。或因時局動蕩,不易形成穩定的社會秩序。
《可樂報告》對考古發掘的現象描述也很仔細。如當地土壤偏酸性,葬具骨骸難以保存,但發掘者根據木痕及漆皮遺跡,仍可推斷出時人是行棺木葬,并使用了漆器。這意味貴州地方使用漆木器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至四世紀左右(如M308)。作者沒有使用制造的字眼,顯得很謹慎,并指出,貴州地方早期的漆器可能是與巴蜀產品的輸入有關。又如,分析制作精美的人物紋圖案銅戈,指出其結構與實戰銅戈明顯不同,根據其出自首領級的墓葬,報告者認為這應當是巫師的法器(150頁)。此可謂真知灼見。因為,圖案中的人物似為作正面蹲蛙形的神人,此與廣西左江花山壁畫人像多作蹲蛙形相類,《準南子?說林訓》就有“鼓造(注:一曰嘏蟆)避兵”之說。
總之,由于發掘者的仔細觀察,表明可樂甲、乙兩類墓葬的主人,其葬俗已受到了內地中原文化的影響,這是前夜郎時期當地族群與內地人民有所交往的開端。因為葬俗中采用漆木的棺槨制度本為殷周文化、巴蜀文化與荊楚文化的特點。又如,發掘者通過對遺跡的分析,還發現墓中有涂撒紅彩的葬俗。
《可樂報告》對眾多的墓葬分作甲、乙兩類描述。甲類墓的數量很少,其隨葬器物大體上可區分為四種:1、本地特有器物(有特點的是各式單耳罐、高直頸圓肩小圜底壺,18頁、28頁);2、滇式器物;3、巴蜀式器物(有銅鍪等,18頁);4、內地漢式器物(有銅帶鉤、五銖錢、漢式菱形劍格、鐵鍤、仿博山爐陶器等,23頁)。甲類墓呈現出復合的文化相,這意味該遺存與周邊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就此,《可樂報告》對其基本文化面貌作了廣泛的比較分析。例如,可樂的墓葬形式雖然與內地中原等 地的墓葬同為豎穴土坑墓,但它更具有川、桂、滇等南方先秦兩漢墓的特點。同時作者還特別強調,可樂甲類墓有個別陶器(BII式罐)與四川石棺葬文化的同類器相似,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為了揭示器物背后的人和史實,作者結合《史記》、兩漢書的有關記載,認為這是漢武帝先后開發西南夷時征發入遷的巴蜀移民的遺存(38頁)。
然而,筆者卻認為這一因素是與氐羌系先民的遺存有關。如可樂的單耳陶罐也較接近川西南米易彎丘、涼山喜德拉克大石墓出土的同類器。結合《史記?西南夷列傳》的記載,當時的夜郎與滇等相鄰的所謂“靡莫之屬”皆為相似的農業民族,與之互動的西邊民族主要是游動的氐羌系民族,夜郎地緊鄰西漢之“k道” (以今四川宜賓為中心),即古代k人的聚居地,《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集解》引晉人徐廣曰:k人,“羌之別種也”,夜郎地區出現氐羌系文化的一些因素,這應當就是不同族群互動的反映。
《可樂報告》指出,可樂甲類墓的出土物以陶、鐵器為主,隨葬較多的漢式銅錢,且多見鐵生產工具,這是與同期相鄰的滇文化偏重銅器、盛行用貝幣有明顯的不同,其時代在漢武帝開發夜郎前、后期之間(元狩五年――元鼎末年或稍后)。這些鐵工具經金相分析,有鑄鐵脫碳鋼、韌性鑄鐵,可根據器物功能選擇使用,反映了西漢中期當地鐵加工技術的熟練程度。不過,報告者又結合占多數的乙類墓出土的銅、鐵器的比例分析,認為當時的鐵器還未能取代銅器的大量使用,這應當是早期使用和制造鐵器的時代特征。此結論事實上是解決了貴州古代史的一個重要問題,即確定了貴州地區進入鐵器時代當在戰國早中期的公元前四世紀左右(如出有銅柄鐵劍、鐵器等,127頁)。又如,可樂出土的鐵戈及柳葉形鐵劍就是在當地生產的仿巴蜀式兵器(103頁)。可樂出土的一批鐵農具,也為漢式,表明它們是由內地中原傳入。
《可樂報告》結合史載,將少數的甲類墓的主人推斷為應募入遷的兵士和“豪民”,即內地的原漢移民。這有較充分的道理,因為最能反映其文化特征的陶器,基本上屬于漢墓器形風格。
另一方面,為了更好揭示出土文物背后的人與事,報告者還注重借助民族學方法。如分析甲類墓的工具鐵(爪鐮)的用途,就借助了貴州從江、榕江一帶侗族、苗族使用的“摘禾刀”與之比證。
三、《可樂報告》與貴州上古民族史研究
《可樂報告》最重要的發現是數量占大多數的乙類墓,即地方民族墓葬。其中反映了豐富的地方民族文化習俗等信息。例如,這些與漢墓有所不同的豎穴土坑墓,規模小,且多呈不太規則的長方形;存在套頭葬俗和其他特殊葬俗。套頭葬俗即是用可樂居民貴重的典型銅器――銅釜置于墓主人的頭頂,這是可樂人區別其他地區民族最奇特的葬俗。此外,還有用石塊壘筑墓坑的個別墓,它使人會聯想到廣西武鳴馬頭先秦墓葬多見的此類習俗。
在其中的套頭葬大墓(M274)所見的巨型銅釜十分引人注目,這一批為數不少的套頭墓葬,其中有9座的時代上限皆可斷為戰國晚期(122頁)。其大銅釜的肩部鑄有兩只威猛的圓雕立虎雙耳。這表明,古代可樂人與相鄰的滇人貴重銅鼓有所不同,也不同于貴重銅鼎的內地中原的漢民族。史載古代的巴濮人有崇虎習俗,今川東等地發現的巴人銅器上,多見有虎紋裝飾主題,但也沒有見過如此生動寫實的虎造型,這表明,古代可樂人與楚國西南之古代巴濮人有相似的崇虎文化習俗,這可為探討戰國晚期“楚將莊F王滇”史跡及可樂人的族源提供一條新的線索。而且,此大墓已使用了棺木葬具,與不見棺木葬具的小墓形成了等級差別。
另一方面,我們從可樂墓葬出土的銅器組合,也發現它與云南的滇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如可樂見有用數量不等的銅洗(盆)作葬具,漢代最有名的“堂狼洗”是產自滇東北的昭通。可樂墓葬出土的銅戈也可以稱為滇式戈,它與滇池地區出土的銅戈如出一轍。此外,兩地互見的器物還有銅釜、銅手鐲等。當然,最能證明墓主人獨特性的還是可樂居民使用的日用陶器。如它的尖突腹單耳圈足罐(CII式)、敞口束頸平底單耳罐(K4:1),均為其特有,也是它與滇文化的最大區別。不過,可樂的陶瓶和D型陶罐卻與云南昭通地區的滇文化遺存很相似。此外,與數量少的可樂甲類墓不同的是,可樂乙類墓的隨葬品偏重銅器,少用陶器,這也同滇文化的葬俗很相似。尤其是銅發釵的大量使用,也足證可樂居民與滇、邛都等族群同為“椎髻之民”。《史記?西南夷列傳》說:“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漢書》作“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扶”,此可樂出土文物可作一旁證。
出土文物多為無言的史料天書,要揭示其真面目,必須要借助許多學科的方法和手段。不抹殺前人貢獻,力圖借助多學科的專家共同解開可樂地下發現之謎,《可樂報告》的作者為此也作出了艱辛的努力。如為了復原出土陶器的制作工藝,不僅請教了遠方同行專家,還借助了自然科學的分析方法。青銅器研究也是如此。如青銅器的失蠟法鑄造工藝,它在近代仍然不失為先進的精密鑄造技術,它在中國何時出現,至今仍然是懸而未決的科技史難題,可樂出土了距今二千多年前用失蠟法鑄造的青銅器,無疑可為解決此問題提供了一個新證。再如,可樂乙類墓出土的兵器鐵戈、柳葉形鐵劍,都是中國現代考古發現中的較罕見例子(156頁),它們反映,可樂居民在戰國時期從鄰近地區引進冶鐵術之后,已能獨創制造出先進的鐵兵器。正如鑒定者指出,可樂出土金屬器的科技考古研究,事實上是豐富了西南地區冶金技術的研究成果,對于闡明該地區上古的冶金技術史提供了又一批可貴的資料(206頁)。此外,通過對出土絲織品等織物的鑒定分析,專家不僅發現戰國到西漢時期蠶絲和麻的使用,還發現了羊毛織物(215頁)。這些都是闡明西南夷民族上古手工業發展水平的有力證據。
復旦大學的專家還對可樂墓葬的出土人骨作了DNA鑒定,雖然目前尚未取得有效的成果,但它畢竟為探明西南夷上古民族的遺傳基因及其種族特征作出了可貴的嘗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有關專家也對遺址的植物孢粉及碳十四年代作了檢測,這對復原當時的生態環境及遺址的斷代都大有助益。
《可樂報告》可解決的古代史問題是多方面的。如文中指出(92頁),史漢所云,巴蜀至黔之夜郎通道,當在秦開五尺道時,但可樂已出土了一批巴蜀式柳葉形青銅劍,可證蜀商“持竊市夜郎”, “賈椎髻之民”富甲一方的歷史,甚至可追溯到戰國中期的公元前三世紀以前(125頁)。可樂甲、乙類墓也出有一批漢式帶鉤,它們大多出自戰國墓(122頁),其也當從巴蜀或楚地輸入。
又如,南方絲綢之路的何時開通,也是一個尚待繼續研究的重要課題。著名學者如方國瑜先生等人認為西南地區當在公元前四世紀已開通了民間道問,然而,汪寧生先生卻認為西南滇地絲織業的產生則晚見于《南詔德化碑》。筆者認為,可樂墓葬(如M277等,117頁)、云南晉寧石寨山等地墓葬已多出有戰國秦漢間的絲織品實物(也見載于《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條),這表明該時期的西南夷各族已熟知養蠶絲織業當為不爭的事實。
《可樂報告》在概述完出土文物之后,總要述“一些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它實為作者研究文物 的心得,極具啟發意義,讀者皆可在此基礎上作進一步的專題深入探討。其中披露的出土文物,尤其可為研究古代夜郎地區的對外交通提供不少可貴的資料。如可樂的玉塊裝飾品,作者指出它最接近廣西平樂銀山嶺等地墓葬所出的玉塊。又如,可樂乙類墓也出土了一批各色瑪瑙裝飾品,貴州不產此原料,其也當為南方絲綢之路的外來輸入品。《史記?南越列傳》說當時的趙氏南越國東西萬余里,西南之滇、夜郎皆臣屬之,出土物亦可證兩地人民早有交往。又如可樂274號墓出有漢文“敬事”印章,字體具有戰國書體風格,該墓屬首領級(153頁),這也意味著當時漢文化對黔西地區已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作者在確定數百座墓葬的分期編年時,也歸納出這些文化遺存的主要特征,即占大多數的可樂乙類墓可代表一個相對獨立的族的共同體。它有套頭葬的獨特葬俗,有一組能代表其自身與眾不同的文化器物,如圓雕雙虎耳大銅釜、帶鏤空卷云紋劍首的柳葉形劍、尖鼓腹圈足單耳罐等,同時它也深受巴蜀文化和滇文化的影響,如它的鼓形銅釜、銅戈,甚至是劍首的鏤空卷云紋也見滇文化。如前所述,其鐵器、柳葉形銅劍、直內三角援銅戈也源自巴蜀地區。雖然作者對墓葬群的遺物和遺跡現象也作了許多推論,但皆言之有據,不屬主觀臆測。如對乙類墓作了四種身份等級的劃分(135頁),卻沒有對其完全定性。可謂立意謹慎。
作為考古及歷史工作者,不能回避的重要問題就是對可樂遺存的地望、族屬及其社會性質作出推斷。報告者認為,可樂遺址出土有西漢“建始”(前33~29年)年號等銘文瓦當和大型衙署建筑遺跡,故可將此地推定為漢武帝時期建立“漢陽縣”之縣治地,這也是言之有據的推論。可樂乙類墓的族屬,報告者仍然是維持前人的觀點斷定其為濮系民族(394頁),即史漢所載之“椎髻之民”。此外,《可樂報告》還將可樂遺存同幾個相鄰地區的墓葬群(如威寧中水、普安銅鼓山)作了文化特征的比較,其結論是:它們盡管處于相鄰近的地區,也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但彼此主要的文化內涵卻分屬于不同的體系(399頁)。
這些分析判斷對于我們理解古文獻中關于古代夜郎地區復雜的族群關系是十分有益的。如《史記?西南夷列傳》載:漢武帝開發夜郎地區時,“乃拜(唐)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余人,從巴蜀i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后來,漢武帝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可樂地區最接近巴蜀之犍為郡中心區,這里是否就是西漢王朝在黔西所置最早的縣治,且歸屬于犍為郡管轄,這都是我們可以考慮的問題。同時,我們也意識到,夜郎國作為一個較大的部落聯盟體,其內部還存在著較多的小邑族群。這從《史記》、《漢書》就可舉出“勞浸”、“靡莫”、“且蘭”、“漏臥”等名稱。
關于可樂墓葬群反映的社會性質,報告者在述評前人的多種觀點之后,最后將可樂乙類墓的社會性質界定為“復雜的酋邦制” (從童恩正之說)。即它不同于奴隸制,又超越了原始氏族制的階段。并指出,即使在漢武帝開發西南夷之后,在當地推行郡縣制,其原有的酋邦制社會結構也未被強行廢除(402頁)。筆者認為這是符合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的判斷,如《漢書?食貨志》載:“漢(元鼎間)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越),番禺(今廣州)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
不過,報告者對于可樂遺存的發現是否可命名為一個新的考古學文化或“夜郎文化”仍然是心存疑慮的。其主要原因是:可樂遺存的發現還不夠典型豐富,其空間分布范圍究竟有多大,目前也是個未知數。何況,墓葬中也未能找到說明墓主族屬身份的直接證據。因此,《可樂報告》只能暫將其界定為“夜郎時代的地方民族文化遺存”。
筆者認為報告上述的初步結論是可以理解的。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認為,可樂考古的發現與研究,對于探索古代夜郎的歷史,還是邁出了關鍵的一大步。這些發現雖然按考古學慣例命名為“可樂文化”或按古族名命名為“夜郎文化”的條件尚未成熟,但它們與夜郎的歷史緊密相關則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從可樂考古遺存的時間和空間分布狀態來看,它都與夜郎國的時空分布相重合。可樂考古遺存的獨特文化面貌既可作為族的共同體存在的依據,同時它不見于夜郎歷史民族區之外,這也意味著它代表的即使不是夜郎的主體文化,也是“夜郎旁小邑”的文化,或為“勞浸”、“靡莫”之屬也未必可知。因為內地中原人由蜀入滇、黔的路線,首先就必經云南昭通(漢之朱提)至貴州威寧、赫章一線。可樂就處于《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唐蒙“從巴蜀i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的地區。
民族考古學探索范文第5篇
關鍵詞:先秦;封土墓;墓上遺跡;等級
中圖分類號:K878.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6-0020-04
本文談及先秦時期的封土墓,首先需確定封土含義,即泛指墓上聚攏的土堆,無論是否帶夯,亦不論大小規模,只要是墓上積土,則皆包括在內。墓上積土在古代文獻之中有墳、丘、冢、封等名稱,但其涵義大體是有區別的,如《說文解字》“墓為平處,墳為高處。”;《方言》云:“大者謂之丘”,《說文解字》“丘,土之高也。大司徒注曰土高曰丘”,丘謂積土高大的墳;《說文解字》“冢,高墳也。土部,曰墳者墓也。墓之高者曰冢。按《釋山》云山頂曰冢。鄭注冢人云,冢,封土為丘隴像冢而為之。”;《說文解字》“大司徒注曰封,起土也。封人注曰聚土曰封”。由此可見“墳”大概是范指墓上有土堆,不論大小皆曰墳;而“丘”當為積土高大的墓;“冢”為墓上有似山狀高大土堆的墳墓;“封”即為聚土之意,所以在此僅以封土墓范指凡墓上存在積土的墓葬。
中國先秦時期墓葬,在東周以前,當如《禮記?檀弓上》孔子所言“古也墓而不墳”,即實行《周易?系辭傳下》所云“不封不樹”之制,東周以降則盛行封土墓。那么中國封土墓產生之前,存在哪些墓上遺跡,其形式是怎樣的?這些問題關系著中國先秦時期墓上遺跡發展演變到墳丘的歷程。墓上遺跡是中國墓葬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為研究中國古代祭祀禮儀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
一、中國夏朝以前是否存在封土墓
舊石器時代的墓葬,僅見于北京周口店山頂洞,為舊石器晚期,這也是中國最早的墓葬,其墓葬只是利用天然洞穴的一部分來安置死者,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說“蓋上世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
“至于到了新石器時代,墓葬已經有了明確的墓葬制度”[1]。據目前的考古發掘墓葬資料來看,新石器時期墓葬以豎穴土坑墓為主,至于封土之跡未見。但新石器中晚期墓上遺跡仍有所發現,如分布于華北北部的紅山文化的積石冢墓,有積石并圍以石圍圈下壓泥質紅陶碎片或彩陶筒形器,也有石圍墻的積石墓[2];另外在浙江余杭縣反山墓地及瑤山墓地都發現了于熟土墩上埋著隨葬大量玉器的墓葬[3];還有位于西北地區的陜西鳳翔大幸村龍山晚期的墓葬中發現M3的墓壙周圍發現了建筑設施[4]。古代墓葬因地域、時代、文化之別肯定會存在著差異性,正如上述考古資料所示,新石器時代墓上遺跡存在不同的形式―積石形式、土墩形式、建筑形式,且這些墓上遺跡都應該與史前原始氏族的祭祀相關,同時也標明墓葬的具置。另外,根據一些民族學資料顯示,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氏族墓葬區中,一些墓葬之上就是以木樁或石塊等來標識墓地。“可以認為在墓上放置樹枝、石頭、陶片、安設木樁、籬笆以及修建簡易柵房等設施,應當就是由‘墓’到‘墳’的演進過程中的中間過渡形式”[5]。當然,紅山文化的積石墓、良渚文化的土墩墓、陜西大幸村龍山晚期的墓上建筑,這些遺跡規格甚高,絕對不會是氏族之中普通成員的墓葬所能享有的葬禮制度,似乎解釋為氏族中地位較高者的埋葬之所更為妥當,那么普通氏族成員的墓葬,似乎更應該是如民族學所講的木樁,石塊等簡易設施來明確墓葬所在地,自然這些墓上簡易設施因時代久遠,考古上難有所見。要之,夏代之前的中國先民就有了靈魂意識,出現了埋葬死者的行為,但墓葬之上堆砌封土還是未見的。
二、夏、商是否存在封土墓
要談夏商是否存在封土墓的問題,則必然要提孔子所說的“古也墓而不墳”,一些學者認為東周之前墓葬之上似乎都實行“墓而不墳”之制。另外,從目前發掘的三代墓葬資料來看,墓上都未發現有墳丘。所以,綜合先秦文獻資料的記載和考古發掘的實例資料,東周以前的墓葬普遍實行不封不樹之制,即“墓而不墳”是可信的。
目前夏代的墓葬有封土的還未發現,但中原地區的河南省堰師縣二里頭遺址發掘出一座大墓,東西長5.2-5.35米,南北寬4.25米,但遭破壞嚴重,該墓正南偏西0.9米處清理出一座大型建筑遺跡,其由廊廡、大門、廣庭、中心殿堂組成[6]。此座大墓與建筑遺跡的時代都為二里頭三期, 發掘者認為這組建筑的功能和殷墟婦好墓的“享堂”同類,是祭祀大墓墓主的“宗”。
當然關于商代是否存在封土墓,學術界一直有不同于“古之墓葬不封不樹”的相關見解和文章。早在四十年代,梁思永先生曾根據河南安陽殷墟西北岡的發掘所得,提出“殷代大墓上大概原來是有墳堆”的看法[7]。到了八十年代初,高去尋先生著文對梁先生的觀點作了進一步闡述發揮,提出商代大墓之上已有墓冢說[8]。九十年代初,胡方平先生又明確提出“商代晚期,我國古代封土墓已經產生形成似乎是肯定無疑的。”[9]其最重要的依據就是在河南省羅山天湖晚商息氏家族墓地41號豎穴土坑墓上, 首次找到了殘存高約30厘米的封土痕跡,發掘者估計原封土高約1.5米[10]。這完全是存疑的“孤證”,同時還不能排除孤證產生的偶然性。所以,證明商代已有封土墓,則必需基于更多的考古新資料的出現。
雖然商代封土墓的存在不能確定,但墓上建筑是肯定存在的,如安陽大司空村墓地,有兩座中小型墓葬的墓壙上有疊壓房基的現象,分別是311號墓和312號墓,另外安陽婦好墓上亦發現墓上建筑設施,可見商代部分墓葬之上應該是建筑有享堂的[11]。另外根據《山東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可知在M205、M203、M206、M207、M214、M4墓室和墓道口發現有殘臺基、臺基基底、夯土墻、夯土墩、柱洞、礎石、散水等建筑設施遺存[12]。《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地面建筑淺析》可知前掌大帶地面建筑遺存的墓葬存在等級差別,如墓葬地面建筑規格、大小的差別與墓葬大小相符合,并且“這些墓都是單獨擁有自己的墓上建筑,沒有數座墓共有一座墓上建筑的現象”“但不是所有大、中型墓都有墓上建筑”[13]。
夏人、商人皆“事鬼敬神”,墓上享堂是后人祭祀先祖墓主人的重要場所,同時也是地面標識物。商代甲骨中有祭祀先王先祖的卜辭,還有安陽小屯宗廟區的祭祀坑,無不體現著殷人濃厚的祖先崇拜思想。從目前的相關考古資料來看,殷商的大中小型墓皆發現過設置享堂類祭祀建筑的,且其中大中型墓葬之上發現較多且建筑規格高,一些小型墓的墓上建筑相對簡易。當然至于商代封土墓還不能完全否定,既然商代墓葬之上能夠有低臺建筑,那么墓上積土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這一問題還待考古的日后發掘驗證。
三、西周是否存在封土墓
依照目前的西周墓葬考古資料來看,“西周墓無封土”是成立的。雖然能夠確切的證明“西周墓上存在封土”的墓葬在考古資料中仍未見到,但郭寶鈞先生于上世紀30年掘的河南浚縣辛村1號墓,并且在6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說“這是一座西周早期墓葬……此墓建造甚堅,全部填土都是黃色夯土。上口之外,更各向外擴筑夯土寬2.5米,厚1.5米,土色和墓室相同”[14],據此推斷,這可能為該墓原先高大封土殘留下來的遺跡,當然不能排除其他成因的可能性。
需要說明的是,中原地區辛村1號墓是可能有墳丘,而在長江下游的皖蘇浙地區發現了大量的堆壘墳丘的墓葬,如安徽屯溪市、江蘇的句容縣、金壇縣,浙江的長興、海寧等,這些墓葬為西周到春秋時期的“土墩墓”[15]。但這種墓葬形制與封土墓是不相同的。“土墩墓”是平地鋪底,而不是穴地挖出墓室。其做法是在平地上鋪上一層卵石,或者是一層紅燒土、木炭鋪地,再在其上放置葬具和隨葬品,然后在堆筑圓形或饅頭形的墳丘。“土墩墓”是古代吳越地區的一種地域性很強的墓葬形制,其在春秋晚期逐漸消亡。所以雖然土墩墓的出現時間可以追述到西周,但因其墓葬形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封土墓,不能以此來說明西周已有封土墓。同時我們也應當謹記,西周的墓葬在地域上需要區別對待,特別是中原地區的豎穴土坑墓與長江下游的土墩墓在墓葬形制和隨葬品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當然,同時我們也得注意到,長江下游地區的土墩墓最終逐漸消亡的時間―春秋末,正是中原地區封土墓開始大量出現發展的時期,中原封土墓之產生發展很大程度上可能深受長江下游土墩墓的影響,即中原地區在保留地下穴室的基礎上,參考土墩墓,在其墓室上加筑封土。
四、東周封土墓
“平王立,東遷于雒邑”[16],東周開始,王權下移,諸侯爭霸。禮者政之輿,政治的變化帶來了禮制的演變,禮崩樂壞,新興的禮樂制度形成并逐漸流行起來,當然這些新的制度必定也會體現于墓葬。考古發掘的春秋封土墓資料也表明,在兩周新舊禮制交替的歷史背景下,春秋初期,中國古代喪葬習俗逐漸突破了舊禮制的約束,開始流行封土墓習俗。
春秋早期封土墓主要見于我國中原地區,這表明春秋初期中原地區已有一定普及程度的封土墓習俗。具體的考古發現有,湖北隨縣桃花坡發現兩座豎穴土坑墓,簡報稱兩墓封土已殘,為春秋早期墓[17];河南光山縣寶相寺北側發現的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簡報稱墓上原有封土高約7.8米[18]。距離黃君孟夫婦墓不遠處,有“天鵝墩”冢,為春秋早期偏晚黃季沱父墓,原封土堆據說有10米多高,后被磚瓦廠取土破環損毀[19];河南信陽五星鄉的平西5號墓為春秋早期墓番國國人之墓,據說該墓原有封土堆,但地表已被磚瓦廠取土破壞,不知其確實高度[20];安徽省舒城縣河口一座春秋墓,墓口和地表之間,發現殘有0.24米厚的封土層,估計原高約2米,再從出土器物來推斷為春秋早期墓[21]。
隨著春秋初期封土墓習俗在中原及各地的普及流行,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一些歷史文獻中出現了有關封土墓的文字記載。《禮記?檀弓上》記載,孔子合葬其父母,“封之,崇四尺”;同篇記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封之謂也。”而《禮記?檀弓下》又載“(吳國)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如以上文獻記載,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光封土之形就有四種之多,封土墓習俗并非才開始出現,而是已經普遍流行。
進入戰國時期,根據現在的考古發掘和調查,戰國各國貴族的封土墓以國君的高墳大墓為其代表,如山東淄博齊故城附近的齊王冢、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附近的燕王冢、河南輝縣固圍村的三座戰國中期魏王墓、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湖北紀山楚冢、河北平山中山王陵等,封土之俗,蔚然成風。但輝縣固圍村大墓之上僅是建筑設施(享堂),而中山王墓之上則是在封土之上修建‘堂’類建筑,這就是說在戰國時期,這些王室大墓之上就存在著三中不同的形制,以高大封土為大多數,另仍存在如商代大墓之上的享堂類建筑,還有中山王墓這樣的在封土之上修建堂的臺榭建筑。至于這些差別所代表的古代陵寢制度的多樣性原因就需要待以后解決了,但若根據宿白先生的《中國古建筑考古學講稿》可知,商周普遍是較低的臺基建筑,發展至春秋戰國秦時則有了臺榭建筑[22],而國君之陵冢是戰國時期才出現的,則大致按這三類墓上遺跡出現的時間早晚來排序,似乎存在著低臺建筑(享堂)-高臺建筑(臺榭)-封土高臺(陵冢)這樣的發展線路。至于戰國時期平民墓葬以南方地區六千多座楚冢來看,“多為貴族上層所享有的特制,一般楚下層貴族-士階層及庶民皆為無封土之墓”[23],所以戰國平民墓封土應當還是“高可隱”,保存困難,考古難覓。
五、結語
墓上墳丘的產生如楊寬、劉毅先生所云,應當是與西周公邦墓為代表的宗族墓地的衰敗,家族墓地的興起相關,另外封土還起著標志作用[24]。至于封土的大小不同,這和古代社會的“明貴賤,別等別”的等級觀念相關。文獻記載如《周禮?冢人》云:“以爵等為丘封之度”;《禮記?月令》曰:“營丘垅之大小、高平,厚薄之度, 貴賤之等級”。因此,死者墓上封土的大小乃是死者生前社會地位、貴賤等級的標志象征。
要之,中國先秦時期,封土墓的產生過程復雜曲折。新石器晚期一些氏族首領等的管理階層墓上存在有墓上設施,但還沒有發現封土形式。這些不同形式的墓上設施應與氏族社會中祖先神、靈魂觀念密切相關,同時墓葬所在之處自然是舉行祭祀的理想場所。夏商時期中國墓上建筑,主要是以享堂(宗)為主,享堂無疑是祭祀先祖的重要場所;中原地區未見西周封土墓,而長江下游地區的土墩墓可能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封土墓大量產生發展的重要因素來源。所以至此“古之不封不樹”還是確切的。東周時期是先秦封土墓發現最豐富的階段,至于到了春秋早期,隨著西周禮制的破壞,家族墓地代替西周公邦墓為代表的宗族墓地,隨之其需要一種新鮮的形式來標識家族墓地中的墓葬,墓上設封土的做法隨之被大量應用,戰國時則發展成高墳大冢,流行盛廣。
參考文獻:
〔1〕王仲殊.中國古代墓葬概說[J].考古,1981(5).
〔2〕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J].文物,1986(8).
〔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J].文物,1988(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J].文物,1988(1).
〔4〕雍城考古隊.陜西鳳翔大辛村遺址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1985(1).
〔5〕夏之乾.從民族學材料探測從墓到墳的演進[J].廣西民族研究,1988(1).
〔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偃師二里頭二號宮殿遺址[J].考古,1983(3).
〔7〕梁思永.河南安陽侯家莊西北岡殷代墓地發掘報告第四章西北岡文化堆積之結構與殷代墓葬在堆積層中之位置[J].考古人類學刊(臺灣大學),(41).
〔8〕高去尋.殷代墓葬已有冢墓說[J].考古人類學刊(臺灣大學),(41).
〔9〕胡方平.中國封土墓的產生和流行[J].考古,1994(6).
〔10〕河南省信陽地區文管會,河南省羅山縣文化館.羅山天湖商周墓地[J].考古學報,1986(2).
〔11〕馬得志,周永珍,張云鵬.一九五三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1955(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M].文物出版社,1980.
〔12〕胡秉華.山東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J].考古學報,1992(3).
〔13〕胡秉華.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地面建筑淺析[J].考古,1994(2).
〔14〕郭寶鈞.浚縣辛村[J].考古學專刊乙種第十三號,1964.
〔15〕張長壽,殷瑋璋.中國考古學?兩周卷[G].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16〕司馬遷.史記?周本紀[O].北京:中華書局,1982.
〔17〕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縣安居出土青銅器[J].文物,1982(12).
〔18〕河南信陽地區文管會,光山縣文管會.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J].考古1984(4).
〔19〕信陽地區文管會,光山縣文管會.河南光山春秋黃季佗父墓發掘簡報[J].考古,1989(1).
〔20〕信陽地區文管會,信陽市文管會.河南信陽市平西五號春秋墓發掘簡報[J].考古,1989(1).
〔2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舒城縣文物管理所.安徽舒城縣河口春秋墓[J].文物,1990(6).
〔22〕宿白.中國古建筑考古學講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