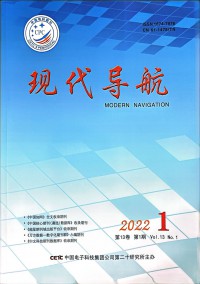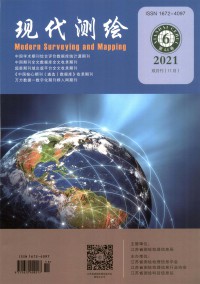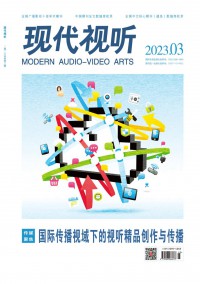現(xiàn)代文化論文范文精選
前言:在撰寫現(xiàn)代文化論文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yōu)秀范文,希望能夠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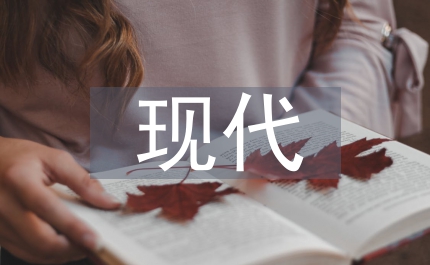
現(xiàn)代文化館室內設計論文
1現(xiàn)代文化館室內設計分析
1.1現(xiàn)代文化館地域化特性
現(xiàn)代文化館建筑與城市的自然環(huán)境、社會發(fā)展、交通生活等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不同城市的經濟發(fā)展、文化習俗、教育結構、人口規(guī)模、生活水平等因素是不同的。各地不同的自然環(huán)境使得城市區(qū)域發(fā)展具有不同的特點,南北方的文化存在差異,其城市建設、文化館室內設計風格也不同。
1.2現(xiàn)代文化館室內空間設計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在文化館室內設計中應用地域文化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2.1缺乏地域文化的創(chuàng)新理念
現(xiàn)代文化理念環(huán)境藝術論文
一、基于現(xiàn)代文化理念的公共環(huán)境藝術設計
現(xiàn)代文化理念對公共環(huán)境藝術設計產生了極大沖擊,如何在公共環(huán)境藝術設計中巧妙融合現(xiàn)代文化理念,使公共環(huán)境藝術設計在更好的體現(xiàn)現(xiàn)代文化理念的同時,不斷滿足時展要求和公眾對精神文化的渴求,成為公共環(huán)境藝術設計的重中之重。那么基于現(xiàn)代文化理念的公共環(huán)境藝術設計應該注意哪些問題呢?
1.設計要做到實用性和公眾審美的高度統(tǒng)一
從公共環(huán)境藝術設計發(fā)展的歷程可以得知,公共環(huán)境藝術設計是一種不同于其它藝術設計的藝術形式,具有一定的獨特性。這種特性要求設計的作品具有高度的實用性和效益性。隨著現(xiàn)代文化理念的介入,實用性的設計原則被置于更高的地位,現(xiàn)代人對環(huán)境規(guī)劃的要求是既要滿足公共環(huán)境設計的功用性也要滿足大眾審美的需求,這就使公共環(huán)境藝術設計要做到實用性和公眾審美的高度統(tǒng)一。只有這樣,人們才可以從環(huán)境藝術設計的作品中,通過調動多種感官細胞,身臨其境地進行一場酣暢淋漓的審美體驗。
2.設計要在確保經濟性的同時關注環(huán)保性
經濟高度發(fā)達的現(xiàn)代社會,將公共環(huán)境藝術設計的經濟性特征置于十分顯眼的地位,因此也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重視。但設計目標在滿足人們經濟效益的同時不可忽視其對環(huán)境帶來的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這就要求人們在進行設計過程中同時關注經濟性與環(huán)保性兩方面內容。環(huán)境公共藝術設計也要遵循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現(xiàn)念,在獲取經濟效益的同時確保生態(tài)平衡十分重要。現(xiàn)代文化理念要求,環(huán)境藝術設計不能單純立足于經濟效益,更要體現(xiàn)對環(huán)境的積極性,以確保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健康發(fā)展。
無名氏研究考察探析論文
[摘要]無名氏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的一位傳奇性作家,是“潛在寫作”的最為典型的代表。無名氏研究在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中是從零開始,隨著對無名氏研究的不斷推進,無名氏及其作品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和接受,無名氏也徐徐進入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無名氏研究包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研究和九十年代的研究及二十一世紀的無名氏研究。
[關鍵詞]現(xiàn)當代文學;無名氏;研究;考察
隨著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過去因種種原因被冷落的作家浮出水面,且引起不少研究者的興趣,無名氏就是其中之一。無名氏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的一位傳奇性作家。無名氏及其代表作《無名書》在現(xiàn)代中國的文學史上是一個獨特的現(xiàn)象,因為對個體生命和人類終極命運作如此思考的人在20世紀的中國只有他一人。無名氏是“潛在寫作”的最為典型的代表,其代表作《無名書》不僅代表了中國20世紀50至60年代潛在創(chuàng)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自新文學運動誕生以來最獨特的小說作品。隨著對無名氏研究的不斷推進,無名氏及其作品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和接受,無名氏也徐徐進入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本文就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無名氏研究作一歷時性考察,試圖從中找出一些思考的問題,以引起研究者的共同關注。
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無名氏研究
由于種種歷史的原因,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年內,中國大陸對無名氏其人其文無人知曉,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像沈從文、張愛玲一樣,國人知道無名氏也是先從海外開始。無名氏得到了香港中國新文學史家司馬長風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專家夏志清教授的高度評價。隨著改革開放,港臺及海外的無名氏之風逐漸傳入大陸。
(一)無名氏作品的出版情況。
五四文藝理論新傳統(tǒng)基礎上接著說
中國現(xiàn)代文學理論如果從1899年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不久之后又提出“小說界革命”算起,已歷盡百余年。誠然,在這百余年之間,有過“全盤西化”的提法,有過以西方文論的馬首是瞻的人物,有過西方文論名詞轟炸的時刻,至今仍有一些年輕的或不大年輕的學者亦步亦趨追趕西方的文論浪潮,這個事實不容回避。但也有比較客觀評介西方文論的著作,把西方文論的術語、概念經過我們的改造,變成中國自己的東西。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百年現(xiàn)代文論的主流是隨著中國時代的變遷而變遷的,它對西方文論話語的取舍,對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取舍,都與時代的發(fā)展和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密切相關,與當下的社會文化狀況密切相關。中國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根”在中國的現(xiàn)實及其發(fā)展中,在中國文學的實際及其發(fā)展中。可以說,從梁啟超、王國維到魯迅、郭沫若、茅盾、宗白華、朱光潛、馮雪峰、胡風、楊晦、黃藥眠、何其芳、錢鐘書、王元化、蔣孔陽、李澤厚等,再到“”時期被批判而活躍于20世紀50、60年代的所謂“黑八論”的作者,諸如秦兆陽、巴人、周谷城、錢谷融等,再到新時期開始后中國當代新文論形態(tài)的建設者,絕大多數(shù)都是立意做本土化的中國現(xiàn)代文論的。
不難看出,中國現(xiàn)代文論經過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繼的努力,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傳統(tǒng)。盡管可能我們較多地借用了西方的一些文論術語,但其內涵已經根據(jù)中國的民族精神、中國正在發(fā)展的現(xiàn)實和中國正在發(fā)展的文藝實際而具有中國的特色。如真實性、典型性、審美、再現(xiàn)、表現(xiàn)、形象、形象體系、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代主義、藝術思維、審美意識形態(tài)、藝術生產、思想性、藝術性、內容、形式、鑒賞、接受美學等等術語,由于與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實際相結合,用以說明和分析與西方不同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它們的本土化特征是很明顯的,也是多數(shù)人所認同的。
就魯迅而論,他在現(xiàn)代新文學的建設中,既創(chuàng)造了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成為現(xiàn)代文學最早一批最具藝術實力的成果,又實現(xiàn)了文學觀念的改造。魯迅的文藝理論完全是屬于中國現(xiàn)代的。這樣說的根據(jù)何在?在魯迅那里,無論是對于西方文論的擇取,還是對于中國古代文論的繼承,都是從當時中國的實際出發(fā)的,針對性很強,他的闡釋糅進了對于中國種種情況的分析和理解,已經有了新的含義,不是簡單生硬地照搬照抄。魯迅主張現(xiàn)實主義文學,特別提出“真實性”的概念,有過多次精辟、深刻的闡述,使“真實性”成為最早成熟的中國現(xiàn)代文論觀念,并對創(chuàng)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為什么這個源于西方的“真實性”概念會最早進入魯迅的視野呢?這是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目標之一是反對封建主義的虛偽的、虛假的、欺騙的和不敢正視現(xiàn)實的弊病,魯迅的“真實性”觀點是在批判封建主義文學的“瞞和騙”的過程中闡發(fā)的。在魯迅看來,“瞞和騙”是違反真實性的,是與藝術相敵對的。1925年,魯迅在《論睜開了眼看》的重要文章中說:“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于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魯迅還重點抨擊中國封建時代的“十景脖和“團圓主義”,指出“十景脖是中國國民性的祖?zhèn)鞑B(tài)之一,這種病態(tài)的要害是掩飾缺陷;“團圓主義”的“曲終奏雅”,則完全是撒謊,是對黑暗現(xiàn)實的粉飾。這些都清楚說明了魯迅的真實性的概念的提出,完全是根據(jù)中國的現(xiàn)實情況所作出的理論選擇,已經有現(xiàn)代的獨立的眼光和立常當一種理論已經扎根于中國現(xiàn)實的土壤中的時候,那么它已經獲得新的內涵,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民族化和本土化了。如果還說這“歸于西方”,那就失去了理論應有的客觀的態(tài)度。再如魯迅對于中國古代文論某些概念的繼承也不是完全的照搬照抄,而是進行現(xiàn)代轉化,使舊的概念獲得新的意義和內容。“形似”與“神似”是傳統(tǒng)畫論和文論的重要范疇,魯迅根據(jù)現(xiàn)代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要求,認為“神似”當然重要,但“形似”也很重要,“神似”與“形似”可以并重,這就超越了中國古代那種單純“文貴神似”的觀念。魯迅對于古典的文化遺產的態(tài)度是“棄其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yǎng)及發(fā)達新的生體”(《論“舊形式的采用”》)。那么根據(jù)什么標準來“棄其蹄毛,留其精粹”呢?這就是中國現(xiàn)代現(xiàn)實的需要。以這樣一種態(tài)度去對待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那么我們就可以獲得新的眼光新的內容。,
在這里,我們還可以簡要解析一個術語個案。中國現(xiàn)代文論引進了“審美”這個詞語,但引進后“審美”的含義已經有很大的變化。在西方,“審美”作為一個概念,大致上就是康德所說的“審美無功利”。但自從王國維在上個世紀之初引進“審美”這個觀念之后,“無功利”的含義已經大大被削弱,而滲入了審美也可以“有功利”的思想。這是由于中國自晚清以來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淪喪為半殖民地的境地,亡國滅種的危險日益迫近,這不能不引起一些有起碼愛國心的知識分子的憂慮。所以他們從西方引進“審美”的觀念,就不僅單是純粹的游戲,完全的逍遙,不能按照西方的“審美無功利”照搬,而要加以改造和變化。王國維提倡審美,一方面也強調文藝審美的獨立性,強調文藝的獨特的功能,甚至也宣揚“游戲”因素,但是他自己又自覺地把“審美”與通過教育改變“民質”相聯(lián)系,審美中不能不夾帶著啟蒙,這里就有了功利目的。自此以后,中國的文論家、美學家一般將審美的無功利與有功利視為可以相容的方面,審美無功利和審美有功利并存。王國維和魯迅都先后提出過藝術“無用之用”、“不用之用”的主張,所謂“無用”、“不用”即藝術審美無功利,所謂“有用”就是藝術審美有功利。20世紀50年代美學大討論,美學家李澤厚就明確審美無功利與有功利統(tǒng)一的看法,這個看法被很多人所采用,蔣孔陽先生也采用這個說法,在許多學者那里一直延續(xù)到如今。可以這樣說,在民族社會矛盾十分突出的時期,審美的“無功利”一端被放到次要的方面,“有功利”的一端凸顯為主要的方面,于是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如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提出文藝從屬于政治,認為文藝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武器”,功利性可謂強矣,但也不是不要審美,只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功利是主要的,但也要藝術,也要審美。這種說法一直延續(xù)到“”時期。新時期開始以來,文藝學界為了糾正“文藝為政治服務”口號的偏頗,根據(jù)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精神,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了文學“審美”特征論,其中有的提出“審美反映”的觀點,有的提出“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直到1999年筆者仍寫了一篇《審美意識形態(tài)是文藝學的第一原理》的論文。所謂“審美反映”和“審美意識形態(tài)”,既強調文學的感性特征,同時又強調文學的理性特征;既強調文藝的無功利性,又強調文藝的功利性。就其實質而言,就是要在文學的感性與文學的理性的緊張關系中取得某種平衡,在文藝審美的無功利與功利的緊張關系中取得某種平衡。這些觀點及其在歷史發(fā)展中的變化都不是完全照抄外國的教條,它針對的是中國的現(xiàn)實,并獲得了中國本土眼光與內涵。不難看出,“審美”這個外來詞,已經成為了中國現(xiàn)代文論、美論的有機的組成部分。關于中國現(xiàn)代“審美”這個關鍵詞如何被引進,如何隨著歷史的變化而變化,如何獲得區(qū)別于西方的“無功利又具有功利”的內涵等等,可以寫出一篇很長的論文來。這個個案分析足以說明中國現(xiàn)代文論雖然用了部分外國的概念,但在在其歷史發(fā)展中,已經獲得了本土化的內涵,成為一個新的傳統(tǒng)。
以上簡要的論述說明,中國現(xiàn)代文論就是符合中國現(xiàn)實發(fā)展和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實際的文論,就是與中國的民族精神結合的文論,它植根于中國自身的民族奮斗的現(xiàn)實中,它是歸于中國的,而并非西方文論的延伸,并不能不加分析就說歸于西方。要是我們中國現(xiàn)代的文藝理論是失語的,是歸于西方的,并不存在中國現(xiàn)代文藝理論,那么社會科學中文藝學作為一個學科,還能不能成立呢?當然,我并不認為中國現(xiàn)代形態(tài)的文論已經完全成熟,它仍在途中。也正因為還在途中,還在發(fā)展中,所以我們覺得創(chuàng)新的必要。如果我們根本沒有“五四”以來現(xiàn)代的文論傳統(tǒng),甚至一點基礎也沒有,根本就不具有“接著說”的前提條件,那么我們的創(chuàng)新就要變成“憑空”說了。根據(jù)我個人的體會,所有的“創(chuàng)新”都不可能是憑空的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在大多數(shù)的情況下是“舊中之新”,而不可能是絕對的“新”。
“原創(chuàng)”可能還會有,但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原創(chuàng)”的時期似乎已經過去。對于文藝理論界來說,我們多半只能在“五四”所開創(chuàng)的文藝理論新傳統(tǒng)的基礎上“接著說”。
淺談我國當代文學中的作者研究論文
[摘要]無名氏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的一位傳奇性作家,是“潛在寫作”的最為典型的代表。無名氏研究在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中是從零開始,隨著對無名氏研究的不斷推進,無名氏及其作品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和接受,無名氏也徐徐進入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無名氏研究包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研究和九十年代的研究及二十一世紀的無名氏研究。
[關鍵詞]現(xiàn)當代文學;無名氏;研究;考察
隨著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過去因種種原因被冷落的作家浮出水面,且引起不少研究者的興趣,無名氏就是其中之一。無名氏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的一位傳奇性作家。無名氏及其代表作《無名書》在現(xiàn)代中國的文學史上是一個獨特的現(xiàn)象,因為對個體生命和人類終極命運作如此思考的人在20世紀的中國只有他一人。無名氏是“潛在寫作”的最為典型的代表,其代表作《無名書》不僅代表了中國20世紀50至60年代潛在創(chuàng)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自新文學運動誕生以來最獨特的小說作品。隨著對無名氏研究的不斷推進,無名氏及其作品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和接受,無名氏也徐徐進入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本文就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無名氏研究作一歷時性考察,試圖從中找出一些思考的問題,以引起研究者的共同關注。
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無名氏研究。
由于種種歷史的原因,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年內,中國大陸對無名氏其人其文無人知曉,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像沈從文、張愛玲一樣,國人知道無名氏也是先從海外開始。無名氏得到了香港中國新文學史家司馬長風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專家夏志清教授的高度評價。隨著改革開放,港臺及海外的無名氏之風逐漸傳入大陸。
(一)無名氏作品的出版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