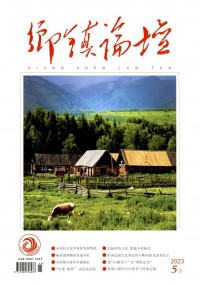鴛鴦蝴蝶派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鴛鴦蝴蝶派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鴛鴦蝴蝶派范文第1篇
[關鍵詞]傳播 鴛鴦蝴蝶派 電影創作
上世紀20年代初,隨著《玉梨魂》、《空谷蘭》《啼笑因緣》等電影的熱播,鴛鴦蝴蝶派逐漸為大眾所熟悉,并引發了一股鴛鴦蝴蝶派電影創作的熱潮。但長期以來,人們在考察文學活動時,只注重了對文學創作、文學文本、文學接受的研究,因此大多數觀眾對鴛鴦蝴蝶派的認識,僅限于知道該派創作是以才子佳人情節為主的市民小說,不登大雅之堂。從實際情形看,內容只是文學活動中比較重要的環節之一,文學所處的社會環境與傳播方式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這些因素綜合促進了文學創作、文學文本和文學接受的全方位變化,使文學活動具備了不同于以往的特點。如果單是從創作文本本身的思想內涵或整體藝術及接受美學等方面加以研究或考察,鴛鴦蝴蝶派的文學創作似乎一直不被學界認可,甚至被視為“逆流”。但當我們把鴛鴦蝴蝶派現象置于當時代傳播的社會環境下,與其電影文學創作、媒體傳播方式和受眾的選擇與滿足等因素相結合,對其派別思想及作品在傳播過程中加以整體的觀照時,鴛鴦蝴蝶派電影創作熱潮的出現又是必然的。
文學創作本身契合電影的大眾文化特色
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產品,要始終得益于文學的滋養。作為文學流派,鴛鴦蝴蝶派就是一個交織著新與舊、現代與傳統的獨特的文學現象。五四時期,魯迅先生領導下的左翼文聯等新文化陣營在批判復古論調的同時,新文學陣營不斷地同鴛鴦蝴蝶派展開斗爭。理由是他們認為鴛鴦蝴蝶派文學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場”,是在失敗后人民開始覺醒的道路上的和迷惑湯。作品大多標榜趣味主義,內容庸俗,思想空虛。然而,理性閱讀鴛鴦蝴蝶派作家的一些作品后,我們卻可以感覺到,這一類作家的所謂靡靡之作,并非全都只是單純的以描寫才子佳人為主,大多表現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思想意識,表現了病態社會中小市民階層的藝術趣味。它們當中不少,比如張恨水的《啼笑因緣》,比如包天笑的《滄州道中》等,或多或少的抨擊了當時社會的黑暗面,諷刺了當時社會的種種弊端,借才子佳人或凄婉或悲涼的戀愛故事,歌頌或贊揚了抗日青年,反映了對當時社會男女不平等、貧富不均等種種丑惡,在當時來說,與其同時代的一些極端宣揚封建復辟、迷信邪說的文學作品相比,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盡管在理論上受到傳統文人的重創,但鴛鴦蝴蝶派仍是現代通俗文化的主潮,具有大眾文化的特色。其作品內容既涉及到大眾普遍喜愛的古典小說、戲曲故事、坊間說書、民間傳奇、稗史俠義等傳統的通俗文學,又吸收了《茶花女》等西洋小說的悲情與浪漫創作。創作標榜文學的娛樂性、消遣性、趣味性,正好迎合市民階層的時尚,擁有極為龐大的讀者群,具有一定的社會基礎。鴛鴦蝴蝶派小說曾是前文學界最走俏的通俗讀物之一。代表作主一徐枕亞的《玉梨魂》曾創下了再版三十二次,銷量數十萬的紀錄。著名作家張恨水的《啼笑因緣》也曾先后十數次再版,其五大作家“張恨水、包天笑、周瘦鵑、李涵秋,嚴獨鶴”的作品在報紙連載時,曾出現市民排隊等候報紙發行的場面,其市場效應遠遠超過新文學作品。
電影是以娛樂大眾為本位的,大眾本身充滿著對“故事”的渴望。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下,流行而充滿活力的鴛鴦蝴蝶派通俗文學就為電影創作提供了豐厚的資源。20年代初,以“明星”公司為代表的中國早期影人開始從深受市民喜歡的鴛鴦蝴蝶派小說中吸收養分。1924年的《玉梨魂》是最早一部改編鴛鴦蝴蝶派小說而取得巨大反響的電影。后來包天笑、周瘦鵑等鴛鴦蝴蝶派文人甚至為電影公司所聘,專門從事編劇工作,早期中國電影和通俗文化的交融自此拉開序幕。繼包天笑之后,許多鴛鴦蝴蝶派文人相繼加入電影創作隊伍,如張恨水、程小青、朱瘦菊、嚴獨鶴、徐卓呆、陸詹庵等等,直接促進了中國電影與通俗文學的聯姻。從1921年到1931年這一時期內,中國各電影公司拍攝了共約650部故事片,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由鴛鴦蝴蝶派文人參加制作的,影片的內容也多為鴛鴦蝴蝶派文學的翻版。
媒介運作加速了電影文學的大眾傳播
大眾媒介從一誕生起就是契合大眾文化的內容要求的,而大眾文化也是契合大眾傳媒的特性而產生的一種文化形態。在對鴛鴦蝴蝶派的考察中,我們會發現,自它興起之初,就與當時的主流傳媒報刊結下了不解之緣,其小說幾乎全部在報紙副刊上連載過。該派的發源地是自由黨人周浩、戴天仇所主辦的《民權報》,其代表人物徐枕亞、吳雙熱、李定夷、何海鳴、蔣著超均為該刊編輯,其代表作《玉梨魂》、《孽冤鏡》等也是首次發表在《民權報》副刊上。其后的周瘦鵑、包天笑、張恨水、劉云若也都是兼具小說家與新聞記者、編輯的雙重身份。他們中多數是在做報業的同時寫小說,或是寫小說前做過媒體工作,或是小說出名后,被聘為多家報紙的編輯。他們的這種文學創作與報刊的雙重互動,使他們的小說與報刊的發行量捆綁在一起,由此也極大的影響了鴛鴦蝴蝶派作家的創作目的和獨特的文學傳播方式。而這種創作目的在與新文學的比較中顯示出了極大的大眾接受優勢。
由于電影不僅是藝術,而且是一種需要大投資的企業產品,它的再創作、再生產是以回籠資金為前提的,所以商業性是其與生俱來的本質特征。在鴛鴦蝴蝶派電影創作出現之前,中國電影的商業化操作更多地借助于商業化的經典文明戲,當時就很快失去了觀眾,失去了市場,使中國電影處境危機。其實不僅僅是出于“故事荒”或“劇本荒”的原因,還有更重要的市場疲軟的原因,后來電影公司與鴛鴦蝴蝶派文人合作,運用傳播的種種技巧,將中國商業電影或中國電影的商業化發展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電影創作上,該派文人先是建立通俗文學敘事模式、創造文學化的影像風格,進一步地創作類型片。從傳播角度,媒體成功運用了傳播學的“議程安排”功能。安排了一系列令公眾感興趣的話題,如“傳奇身世”、“文化漢奸”、“小資愛情”等,以探尋、爭鳴、或獵奇等形式,層出不窮、鋪天蓋地般出現于報刊、電影熒屏等眾多媒體。
鴛鴦蝴蝶派創作內容上是通俗易懂的,而不是像經典文學那樣陽春白雪、曲高和寡,離普通大眾很遠。傳媒為了追求生命力和活躍性,形式也不斷的變換花樣,求新求變。再經過大眾口耳相傳,創作者、傳媒與接受者形成了面對面的接觸關系,使傳播不僅 僅是文學活動,而且具有密切的人際交流性質。
另外,近代城市大眾媒體的建立和完善,也為鴛鴦蝴蝶派電影創作成為流行提供土壤。從19世紀中葉副刊出現后,大眾傳媒刊登文學作品成為一個普遍現象,中國文學傳播也隨之呈現繁榮景象。該派小說首先是在副刊上連載,后又因為各種原因持續不斷地成為媒體上的熱門話題(如《玉梨魂》就有單行本的版權糾紛),造成了小說的暢銷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除了電影,當時時興的新劇也都從流行的小說中尋找題材。1916年吳雙熱的《孽冤鏡》被編演為新劇,同時,民興社也祀《玉梨魂)搬上了新劇舞臺。這些成功嘗試在很大程度上對后來的電影流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由此帶引鴛鴦蝴蝶派電影、海派電影乃至中國電影開始真正走向商業和藝術的雙向成熟。
受眾的選擇與滿足引發新的文學傳播方式
從大眾接受的角度考慮,鴛鴦蝴蝶派為吸引受眾,他們從內容到形式無不考慮庸俗化、世俗化、故事化。他們是打著“游戲”、“消遣”的旗號登堂入室的。因此,題材上涉及言情、哀情、社會、黑幕、家庭、武俠、偵探、滑稽等各種普通市民喜愛的類型,以達到受眾娛樂消遣的目的;創作方式上,該派文人通過建立通俗文學敘事模式,繼而與當時剛興起的電影這一傳播渠道相結合,用一種文學化的影像風格,創造了受眾樂于接受的創作類型影片。
鴛鴦蝴蝶派的受眾是廣泛而穩定的。他們的接受者,有文化層次較高者,也有更多的普通市民,甚至一些文盲、半文盲也產生了接受與傳播的熱情。這些普通大眾大多生活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大都市中,尤其在上海最為集中。都市生活將人們從那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辛勤勞作的生活中解放出來,并且使人們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滿足。人們不再需要擔心生存威脅而終日惶惶不安,心境開始進入一種閑適狀態,消遣與游戲是此時最合適的放松方式。鴛鴦蝴蝶派的電影創作正好是與大眾心理需求及接受方式相契合的。從清倌人到先生的變化,花酒的程序與人物的種種作態,各種游樂場所的聲色犬馬,租界的繁華,政界的權謀之術……種種物與人的社會相,在鴛鴦蝴蝶派作品中都可一覽無余。加之通過電影這種新興傳播渠道,為人們提供多種多樣的視覺傳播系統,普通大眾通過觀賞這些作品,他們從中找到了釋放生存焦慮的出口,得到了極大的感官刺激和心理滿足。畢竟,這是他們關心的并能與他們產生共鳴的世界。因而,與其說是鴛鴦蝴蝶派作品造就了一批消遣型受眾,不如說這是絕大多數市民的自覺選擇,普通市民大眾樂于也安于作此種受眾。
鴛鴦蝴蝶派反復強調“以己身作為讀者”、“讓讀者去研考”,有時,還公開向受眾征集素材。這種時時刻刻不忘受眾、與受眾不斷溝通的創作宗旨,使文學走向大眾邁出了重要一步。當時紅極一時以致被改編為電影達6次之多的《啼笑因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時的上海市民見面,常把該影片中的故事作為談話題材。雖然傳統的文學觀念一直排斥該派創作,并斥之為“不登大雅之堂”,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鴛鴦蝴蝶派不但從內容上獲取了大量自己的受眾,在雅俗共賞方面確實也取得了成效。該派文人采用新的傳播渠道――電影,無形中建立一種適合都市商業運作機制的文化形式,它的類型化影片操作(小說人物、故事、道德以及形式的類型化)得它比較容易找到固定的消費者。同時,通過嘗試,它實際上已經建立起某種形式的文化市場:一定的傳播者同一定的受眾之間的良好供求關系。從這層意義上來說,鴛鴦蝴蝶派所建立的文學作品與大眾傳媒之間的共同關系,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互動關系,不但是文學傳播方式的轉變,也給都市生活創立了新的大眾文化形式。
鴛鴦蝴蝶派范文第2篇
起初,劉春霖參加光緒甲辰的恩科考試時,光緒皇帝已被幽居在了瀛臺。考試之后,主考官把選出來的前幾名考生的卷子進呈慈禧太后觀看。看到進呈的10本卷子中的第一本的考生名字是朱汝珍,此時的慈禧太后早已把光緒皇帝寵愛的珍妃看成眼中釘,所以,慈禧太后看到朱汝珍名字中有一個“珍”字,就很不高興。于是,慈禧太后就把劉春霖選拔為這次考試的第一名,也就是狀元。慈禧太后對主考官說,如今連年干旱,還是祈求上蒼,早降甘霖吧!慈禧太后一言九鼎,誰也不敢違抗,所以,劉春霖便大魁天下,成為清朝最后一個廷試中的一甲第一名。后來,人們就稱他為“末代狀元”。
后,清朝被,進入了民國時期,這時的劉春霖住在北京西城,作了一名寓公,因為畢竟是狀元,劉春霖名尊位高,雖然以賣字度日,生活也過得頗為優裕。
當時,上海富商哈同作古后,特意禮請末代狀元劉春霖點神主,以示隆重。
后來,民國時期“鴛鴦蝴蝶派”中的言情作家徐枕亞成了劉春霖家的東床快婿。
徐枕亞是江蘇常熟人,民國初期,他就因為寫了言情小說《玉梨魂》而成名。徐枕亞名覺,字枕亞,別號徐徐、泣珠生、東海三郎等,他10歲就能作詩填詞,在校期間已寫詩800多首,又試寫短篇小說和雜文。1912年初,徐枕亞應周浩之聘,赴上海做了《民權報》的編輯。《玉梨魂》這部風靡一時的言情小說就是這個時候寫成的,并連載在《民權報》的文藝副刊上,一鳴驚人。很快,《玉梨魂》又出版了單行本,并前后重版三四十次,銷量數十萬多冊,風行海內外,并被搬上了銀幕,從而成為“鴛鴦蝴蝶派”影響最大的代表作品,也成為民國時期影響極大的一部文言言情小說,徐枕亞也一躍成為了當時著名的言情作家。《民權報》被政府強行停刊后,徐枕亞進入中華書局任編輯,編撰了《高等學生尺牘》。1914年,徐枕亞改任《小說叢報》主編,因《玉梨魂》備受歡迎,徐枕亞又將其改為日記體,取名《雪鴻淚史》,在《小說叢報》上連載,其受讀者歡迎的程度不亞于《玉梨魂》。此后,《玉梨魂》和《雪鴻淚史》二書并駕齊驅,久傳不衰。后來,由于《小說叢報》社的內部人員發生了意見分歧,徐枕亞于1918年離開了《小說叢報》,自辦清華書局,并創辦了《小說季報》雜志。
徐枕亞的《玉梨魂》是一部言情小說,被視為“鴛鴦蝴蝶派小說的祖師”,它描述了一個凄美哀婉、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玉梨魂》中的青年何夢霞,應校董秦石癡之聘,任教于石湖小學,課余又為遠親崔元禮之孫鵬郎授課。鵬郎幼年喪父,他的母親梨娘年輕守寡,對何夢霞萬分感激。一日,梨娘在園中賞景,見書齋外新豎“梨花香冢”的小墓碑,不禁自感身世,潸然淚下。原來,這個花冢是夢霞惜花所筑。何夢霞和梨娘兩人相見交談,由相憐而相愛。不久,夢霞向梨娘求婚,并表示非梨娘不娶。梨娘不愿逾越寡婦守節禮教,又恐貽誤夢霞,欲投河一死以謝知己,幸被鵬郎追回。后經梨娘勸說,公公作主,將小姑筠倩嫁與夢霞。何夢霞和筠倩兩人勉強成婚,夫妻間感情淡漠,梨娘自悔又鑄大錯,憂慮成疾。時北方發生戰事,夢霞因婚后郁郁寡歡,在秦石癡激勵下投筆從戎。梨娘見筠倩力贊其行,愈益痛心,病篤身亡。臨終的梨娘遺書夢霞、筠倩,筠倩方知寡嫂梨娘為己而死,深感其情,偕鵬郎親赴戰地找尋何夢霞,卻遇到何夢霞住院養傷。何夢霞讀了筠倩帶來的梨娘臨終寫的信,始知梨娘的苦心,從此夫妻相互敬愛,言歸于好。《玉梨魂》寫得繾綣多情,連東南亞的讀者也為之著迷,據說,魯迅的母親也甚愛《玉梨魂》。
劉春霖有個女兒讀過了徐枕亞寫的《玉梨魂》后,更是著了迷,她竟然想和才情洋溢的徐枕亞結成夫妻,因此,她不覺懨懨地生起病來。劉春霖聞知女兒憂思成病,覺得蹊蹺,就要女兒直說心事。女兒沒說什么,只是在枕頭邊取出一本《玉梨魂》遞給父親劉春霖看,眼里卻流出淚來。老狀元劉春霖從沒讀過《玉梨魂》這種書,他翻了幾頁,不禁拍案叫絕,說道:“不圖世間還有如此才子。”劉春霖也喜歡上了徐枕亞的才華,于是,劉春霖立刻托人去找徐枕亞,替女兒說媒。
鴛鴦蝴蝶派范文第3篇
關鍵詞:近代報刊;近代文學;作家;讀者
中圖分類號:G21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72(2010)06―0080―03
學術界早就注意到近代報刊對近代文學的影響:阿英《晚清小說史》(作家出版社1955)指出新聞事業的發達刺激了需要,《晚清文藝報刊述略》(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詳細梳理了晚清文藝報刊的情況。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全面梳理了近代文人與報刊的基本情況。包禮祥《近代文學與傳播》(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討論了各種文體的創作與近代傳播的關系。蔣曉麗《中國近代大眾傳媒與中國近代文學》(巴蜀書社2005)探討了近代傳媒對近代文學言述方式、傳播方式、文體、流派的影響。
梁啟超說:“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曹聚仁也說:“中國文壇和報壇是表姊妹,血緣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文化史,從側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機器發達史;而一部近代中國文學史,從側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聞事業發展史。”誠如局中人所言,近代報刊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近代報刊作為一種公共資源,被近代知識分子充分利用,改變了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當然也改變了中國文學。因為文學發表途徑和傳播方式的改變,文學創作、文學作品的體式和內容也隨之發生變化,近代文學與古代文學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近代報刊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文學場”,為近代文學的發生發展提供新的文化語境,創造了新的生存空間。所謂“文學場,就是一個遵循自身的運行和變化規律的空間”。文學場的生成一般應具備幾個條件,即創作主體自主性的獲得、象征財富的市場的激勵以及雙重結構的出現(包括外部結構和內部結構)。而文學場的內部結構,“就是個體或集團占據的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結構,這些個體或集團處于為合法性而競爭的形式下。”組成文學場內部結構的個體或集團包括文學賴以發生和存在的報紙、雜志、出版機構以及具有近代意識的作家。近代報刊不僅為近代文學的發生開拓了傳播空間、表現對象以及廣大讀者群體,也培養了近代作家的近代意識。
一、近代文學傳播空間的拓展:繁榮的物質基礎
毋庸諱言,近代報刊的產生主要并不是為了文學。洪仁拜在《》中提出“設新聞館”,旨在“收民心公議,及各省郡縣貨價低昂、事勢常變。上覽之以資治術,士覽之得以識通變,商農覽之得以通有無”。陳熾《報館》除申明意識外,也強調“達君民之隔閡”。陳衍從張國勢的角度提出中國宜設洋文報館,王韜以報紙能“知地方機宜”、“知訟獄之曲直”、“輔教化之不及”,主張“各省會城宜設新報館”,梁啟超認為報館能夠“去塞求通”。1896年6月12日,李端提出“廣立報館的主張”,旨在“通今”。孫家鼐認為“報館之設,所以宣國是而通民情”。總之,是為了通達上下之情和國家富強。
從實際看,最早的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是為了“成人德”,使人明“神理”、“人道”、“國俗”。《特選撮要》也是為了使民眾明道理,“修德從善”。傳教士辦報刊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傳教。改良派、革命派主辦報刊是為了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如《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宣傳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的改良主張,《民報》、《民呼報》、《中國日報》等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革命思想。商人辦報則是以提供信息服務來謀求經濟利益,如《申報》、《上海新報》。文藝報刊固然是為了文學而生,但也還有附帶上述三種目的。《新小說》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寰瑣記》、《海上奇書》、《繡像小說》等有明顯的經濟利益訴求,《言》顯然有傳道色彩。
由于文學特別是小說有“淺而易解,樂而多趣”的美學風格和審美功能, “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梁啟超語),傳播者為了實現他們的目的,都借助文學,從而拓展了文學的傳播空間。傳教士的報刊為了拉近與中國讀者的距離,用中國古典文學的形式或寫法進行寫作,并且刊登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為了表明其宗教的可取和文明的先進,刊登他們國家的文學作品,以為夸耀。從最早的中文報紙擦世俗每月統紀傳》,到影響中國士人甚巨的《萬國公報》,莫不如此。改良派和革命派則主要是因為言禁,為了取得更好的宣傳效果,借助文學作品進行政治宣傳。如梁啟超“專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商業報刊一方面是因為言禁,另一方面是為了節約成本,大量發表文學作品。三股合力使得近代報刊幾乎都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極大地拓展了文學傳播的空間。
據不完全統計,1815年到1911年中文報刊有1753種,其中多數刊登過文學作品。這不僅突破了古代文學作品僅僅靠總集、合集、別集和口傳的束縛,也極大地刺激了對文學作品的需求。近代文學的產量之巨是學界公認的,無論那種文體,其數量均遠軼前代,造成近代文學的繁榮。不僅為了適應報刊的需要和特點產生了新的文體,如新學詩、新民體、各種小說,也使得衰老的一些文體如詩鐘、燈謎等獲得了廣闊的傳播空間。
袁進指出:“凡是近代的進步文人,大抵都與報刊發生關系。”應該說,近代文人絕大多數與報刊結下了不解之緣。王韜、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于右任、魯迅、吳趼人、譚嗣同等進步文人如此,孫玉聲、袁祖志等舊文人,李涵秋等鴛鴦蝴蝶派作家也是這樣。
王韜(1828-1897)是近代由傳統知識分子成功轉型的傳播者。他18歲成為秀才,旋因鄉試不中,1849年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聘,在墨海書館編譯西方自然科學書籍,編輯《六合叢談》;因政治原因逃到香港后,助人翻譯經書,主編中文報紙《近事編錄》,后為《香港華字日報》撰稿,并于1874年創辦《循環日報》。
梁啟超在《創辦原委記》中記述了這種混同的情況。包天笑等公開刊登啟事征求小說材料,吳趼人、李伯元等的自我表白,也能夠充分說明這種狀況。身份混同使作家在寫作時混淆或忽略文體的區別,把消息、議論、說明等文體承載的內容放到文學作品中,用非文學的寫法進行文學創作,新民體、新學詩、政治小說、社會小說、黑幕小說等就是
這樣的產物。這種作品借報刊強大的影響力,迅速被模仿,這是新民體、鴛鴦蝴蝶派作品風行的主要原因。小說戲劇等敘事文體的繁榮,成為文學之最上乘,主要得益于此。近代文學風尚形成快、轉變也快,亦根源于此。
但身份混同使近代作家更接近社會現實,視野開闊,能夠比較容易地獲得創作素材和創作沖動。一方面使文學更加關注國計民生,作品反映的社會與人生更為廣闊;另一方面則令作家放棄精雕細琢,影響作品的質量。
三、讀者劇增:干預或參與創作
報刊既經創辦,就要求生存、求發展,不管是為了經濟效益,還是為了宣傳效果,都必須盡力爭取盡可能多的讀者。因此,各類傳播者在發行上都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計擴大發行量。當時報紙的發行方式多種多樣,主要有:自辦發行(報童、分銷處)、郵局發行和中介代銷及三者相結合。刊載文學作品既是擴大發行量的有效手段,但刊登著文學作品的報刊也為文學作品培養了大量讀者。傳教士所辦的擦世俗每月統紀傳》初印500冊。后增至1000冊,最高達2000冊; 《萬國公報》創刊時每期發行1000冊。M邇貫珍》每期印3000冊。商業性的《申報》創辦不到1年就可賣3000份,1877年達10000份,其后更達數萬份。宣傳政見的《時務報》、(清議報》、慚民叢報》、K報》、 《民報》等均在創辦不久就銷數過萬。許多文藝性的報刊發行量也很可觀,《減寰瑣記》創刊時銷2000冊。而且報刊的流動性、共享性比書籍強,其實際讀者的數量比發行量還要大,這個讀者數量是過去的作者不敢想象的。大量的讀者使作家可以以寫作為生,并激發他們的創作激情。
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編輯、讀者聯系的便利和必要,讀者能夠影響創作。讀者的參與使一些作家改變創作計劃,變更故事情節,改變人物形象,影響了作品的統一性和張力。這是一些近代文學作品質量不夠高的一個因素。讀者的文化素養與傾向,使近代文學更為世俗化,這也是近代文學作品高雅精品較少的一個因素。讀者轉變成為作者的例子很多,有章太炎、王國維等學者型作家,更多的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后者無疑降低了近代文學作品的文化意蘊,加強了世俗性。
四、職責相近:近代作家近代意識的形成
關于報刊的職責,近代不同政見的傳播者的認識有著驚人的相似。梁啟超在(敬告我同業諸勘中指出,報紙有兩大天職:監督政府,向導國民。革命派的件)州日報》同樣認為報館天職“于齊民,須為其導師,而于政府,須為其監史”,報館任務是監視政府,為民請命。”’
這里所說的“國民”,應該是指以隨著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而形成的現代市民階層為主的全體公民。市民階層的獨特生活方式,形成了他們獨特的生活觀念、文化觀念和文化需求,傳統的藝術形式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各種文化需求,近代報刊的出現滿足了他們,從這些報紙上不僅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新聞,因為“凡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日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與夫一切可驚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聽聞者,靡不畢載。”,“呸可以看到生動、有趣的小說,近代報刊由此被市民階層所接受。
鴛鴦蝴蝶派范文第4篇
要賞鑒動人的景致,莫如北海。湖面讓厚冰凍結著,變成了一面數百畝的大圓鏡。北岸的樓閣樹林,全是玉洗的。尤其是五龍亭五座帶橋的亭子,和小西天那一幢八角宮殿,更映現得玲瓏剔透。若由北岸看南岸,更有趣。瓊島高擁,真是一座瓊島。山上的老柏樹,被雪反映成了黑色。黑樹林子里那些亭閣上面是白的,下面是陰暗的,活像是水墨畫。北海塔涂上了銀漆,有一叢叢的黑點繞著飛,是烏鴉在鬧雪。島下那半圓形的長欄,夾著那一個紅漆欄桿、雕梁畫棟的漪瀾堂,又是素絹上畫了一個古裝美人,顏色格外鮮明。
五龍亭中間一座亭子,四面裝上玻璃窗戶,雪光冰光反射進來,那種柔和悅目的光線,也是別處尋找不到的景觀。亭子正中,茶社生好了熊熊紅火的鐵爐,這里并沒有一點寒氣。游客脫下了臃腫的大衣,摘下罩額的暖帽,身子先輕松了。靠玻璃窗下,要一碟羊膏,來二兩白干,再吃幾個這里的名產肉沫夾燒餅。周身都暖和了,高興得渡海一游,也不必長途跋涉東岸那片老槐雪林,可以坐冰床。冰床是個無輪的平頭車子,滑木代了車輪,撐冰床的人,拿了一根短竹竿,站在床后稍一撐,冰床“哧溜”一聲,向前飛奔了去。人坐在冰床上,風“呼呼”地由耳鬢吹過去。這玩意兒比汽車還快,卻又沒有一點汽車的響聲。這里也有更高興的游人,卻是踏著冰湖走了過去。我們若在稍遠的地方,看看那滑冰的人,像在一張很大的白紙上,飛動了許多黑點,那活是電影上一個遠鏡頭。
走過這整個北海,在瓊島前面,又有一彎湖冰。北國的青年,男女成群結隊的,在冰面上溜冰。男子是單薄的西裝,女子穿了細條兒的旗袍,各人肩上,搭了一條圍脖,風飄飄地吹了多長,他們在冰上歪斜馳騁,做出各種姿勢,忘了是在冰點以下的溫度過活了。在北海公園門口,你可以看到穿戴整齊的摩登男女,各人肩上像搭梢馬褳子似的,掛了一雙有冰刀的皮鞋,這是上海、香港摩登世界所沒有的。
(摘編自《煙雨紛繁,負你一世紅顏》
北京理工大出版社2013年1月1日)
鴛鴦蝴蝶派范文第5篇
兒童文學呼喚杰作 周晴
時尚雜志的危機與轉型 尹曉冬
一場永遠新鮮的馬拉松接力賽 李霞
耕作在《國際象棋小世界》 李昂
直面挑戰的《上海譯報》 任玲
古代出版商的讀者服務意識 施勇勤
編輯應堅持寫作 許宇鵬,陳吉平
策劃精品圖書的方法 馬根娣
圖文類圖書版式設計芻議 應黎聲
科技類圖書中自然科學名詞的規范化應用 何劍秋
引文審讀『盲區及滅錯對策 羅時嘉
科技論文編輯規范與習慣用法的協調 陳智
圖書宣傳要突出個性和創意 陳增爵
高校學報編輯應增強學術規范意識 暢引婷
重提高校學報的辦刊宗旨 吳勁薇,沈志宏
青春類雜志的辦刊特色與不足 孔明珠
從人文關懷的視角論女性期刊定位 賀強
少兒報刊開展創新教育之我見 呂江虹
科技期刊英文標題的規范化問題 熊春茹
著錄英文參考文獻應注意的兩類問題 倪東鴻
《漢語主題詞表》存在問題分析 劉春林
實踐最好從踏實開始--讀《清華精神九十年》 汪家熔
關于新版《柳如是別傳》的校訂 陳福康
網上圖書宣傳在美國 王蕾
國家地理學會與《國家地理》雜志 員榮亮
幾宗出版業民事案的辦案啟示 余震琪
委托作品內涵及版權歸屬 岳楠
難忘徐遲 陸潛
文化使者在上海伴侶相依的英美--李約瑟與魯桂珍·聶華苓與安格爾 陸潛
以后的出版研究(下) 張志強
鴛鴦蝴蝶派與中國近代出版 王建輝
《書目答問》傳世百年三論 徐雁
我國近代地圖出版業的文化貢獻 李明杰
總目錄
創新、品位和壓力--獲獎編輯的追求 群明
蝴蝶效應和青蛙效應--中國出版重整格局 陳紀寧
老樹春深更著花--《唐詩三百首》圖文本成功的啟示 高克勤
難道我們只能做"羊"?--淺談經濟期刊如何應對WTO 牛國鋒,牛瑾
創造出版業的基因多樣化優勢 劉楊
向世界貢獻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家--中國出版人肩負的使命 王聯合
編輯的知本與知本的激活 楊曉鳴,沈國明
期刊發展的大趨勢 歐陽志剛
編輯意識、策劃意識、主體意識 楊闖
突破"圍城"天地寬 陳儒林
拓展品牌營銷的空間 朱勝龍
編輯逆向思維四步曲 何其捷
暢銷書、長銷書、版權交易 向洪
中華書局的成功經營之道 吳永貴
小圖書大策劃 張麗珍
可讀性和必讀性 楊青
兩部巨著中的一點美中不足 陳福康
從《革命烈士遺文大典》談思想政治讀物 徐保衛
當"巨石轟然墜落"時 孫歡
"防火墻"與"橋頭堡" 孫梅
可敬的韋老太 吳道弘
大學出版與出版大學 賀圣遂
論出版集團的跨媒體經營 陳可
高校學報如何與國際期刊接軌 吳成福
出版業網絡營銷的策略 江翠平
論期刊主編決策活動 吳成福
甘霖灑大地--任大霖與兒童文學編輯出版工作 周晴
品牌·讀者·五度 徐錦江
"雙校論"小結韻言 孫培鏡
出版時尚化種種 楚山孤
平面媒體錯位傳播現象透視 劉玉清
新聞類周刊的現狀與發展 陳亦駿
學生刊不必爭搶同一塊奶酪 李凌芳
版面設計的加法與減法 王天真
關于上海"出版工作室"的調研報告 舒途,逸青
戰爭考驗傳媒--伊拉克戰爭報道回眸 趙曉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