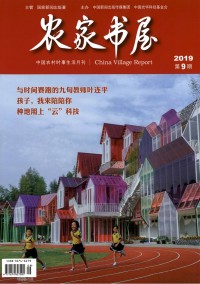故鄉的女孩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故鄉的女孩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故鄉的女孩范文第1篇
小娟是個漂亮的孩子,大大的眼睛,潔白的牙齒,兩個辮子高高地翹著,清秀蒼白的面孔上浮現著燦爛的笑容。我們的車子剛剛停穩在關愛中心門前,我就注意到了她,不高的個子,在媽媽的陪同下,她朝我們跑來,看得出她是歡迎這群不速之客的,裙角飛揚,有如天使一般的她,此時恐怕早已忘記了病痛。
小娟是5月20日在“朵朵向善”幫助下住進北京市通州區兒童關愛中心的,現在她和媽媽一起為這里收留的無家可歸的孤兒和智障兒童服務,當起了小“義工”。關愛中心的經濟情況并不好,除了現有的幾名教師和義工外,無法吸引新人加入。正因為如此,小娟“老師”每天的“工作”都是滿滿的:她要給智障兒童講故事,教他們畫畫,帶著他們唱歌、跳舞;還要擔負起家庭教師的重任,教小孤兒夢雁寫字、制作手工藝品。很快她就和中心的小伙伴們打的火熱,像是相處多年的朋友。
“孩子們都很喜歡她,都愿意和她一起玩”,關愛中心的負責人告訴記者。
“我覺得志愿就是無私,不管怎么樣都要幫助別人”,小娟對于“志愿”的解釋,如此稚氣,但卻十分堅定,“我覺得在幫助他們的過程中我能得到快樂,我給他們快樂,他們也給我快樂。”
也許是剛剛睡過午覺,小娟她看上去并不十分疲憊。笑起來的時候,完全是―個健康快樂的孩子。她的豐治醫生告訴記者,醫學上稱小娟的病為再生障礙性貧血,人們常把它歸人“白血病”,事實上這是一組由多種原因引起的骨髓造血功能衰竭的綜合病征,致死率高達80%,最好的治療辦法是進行骨髓移植。現在盡管她和媽媽的骨髓配型成功,但高額的手術費用對他們來說無疑是―個天文數字。
“真的不想活了!”
“真的不想活了!……我不想每天以藥代飯,不想每天依靠打針維持著呼吸,更不想看到爸爸媽媽一籌莫展、無家可歸的樣子……那一刻我把生命看得很淡很淡。”在小娟的日記里,記者看到以上這些內容。
小娟的母親王文明告訴記者,小娟生病前十分活潑,能唱能跳,生病以后就再也沒有唱過歌了。2005年9月底,學校迎國慶節目正有聲有色地進行著,作為主持人的小娟突然倒在了舞臺上,臉色蒼白,全身發燙。
“病來得十分突然,竟然沒有一點征兆!”小娟的媽媽說,“她爸爸剛聽到這個消息時一動不動地愣在原地,好像傻了一樣。我撲到他身上使勁地搖他,他還是一動不動。我拼命喊了他很久,眼淚才開始從他的眼眶里滑下來,后來他就放聲大哭起來。這一幕,我永遠記得。”
“也就是從那天起,我們沒有睡過一天好覺。她情況不好,我們就為病擔心;情況有了好轉,我們又為下一輪治病的錢擔心。孩子難受了也不敢告訴我們,一個人待在屋子里,怕再給我們添心思。”懂事的小娟輕輕拭去了媽媽眼角的淚水。
小娟一家住在內蒙古通遼的農村,家里本來就不富裕,只能勉強維持生計,小娟的病更是令他們的家境雪上加霜。“家里能賣的都賣掉了,所有的親朋好友都借了個遍,最后只能用房子抵債,現在我們一家三口真的是無家可歸了。”說話時,媽媽的眼睛望著遠方,似乎在尋找家的影子。
就在小娟患病的第:二年春節前期,她又一次因為長時間昏迷被送進醫院。“醫生告訴我們,如果不馬上進行骨髓移植,再一次昏迷可能就永遠醒不過來了。可是手術費用要30萬元,我們無論如何也弄不來那么多錢啊!”“當時,我腦子里空空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疼。我對不起孩子,除了放棄:治療,我們簡直無路可走。就算去賣血,就算把我們兩個大人的血都賣光,也抵不上30元萬啊……孩子這么小,為什么讓她承擔這么多,我們做大人的無能啊……”記者輕輕地將紙巾遞至母親潮濕的手心,不忍再看媽媽的眼睛。
“再等就來不及了!”
幾經周折,小娟從內蒙,輾轉沈陽、天津,最后住進了北京兒童醫院的病房。在醫院里,小娟意外地結識了“朵朵向善”博客團的叔叔阿姨們。
“朵朵向善”是專門幫助患有白血病、再生障礙性貧血等疾病兒童的群體,在幫助小娟之前,他們已經為―個叫婷婷的白血病女孩籌齊了30萬元的手術費用。在他們的幫助下,小娟的治療費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母女倆也搬進了現在的新家。
“現在我和小娟在北京治病,她爸爸―個人在老家打工,定期匯些錢過來。10天前,我們剛在好心人的幫助下來到這家愛心中心。不管怎樣,總算是有個可以睡覺、吃飯的地方了。”小娟的母親告訴記者,“我們來北京時住的地下室只有4平米,孩子本來呼吸就困難,在那里小娟經常因為缺氧憋的喘不過氣來。現在真好,只是麻煩你們大家了。”
故鄉的女孩范文第2篇
槐花:別名刺槐花。為落葉喬木。羽狀復葉互生,先端尖,基部闊楔形,疏生短柔毛。圓錐花序頂生;萼鐘狀;花冠乳白色,有短爪,并有紫脈,翼瓣和龍骨瓣邊緣稍帶紫色,不等長。味微苦澀。涼血止血,清肝瀉火。
在五月的枝頭上,一串串綴著的潔白風鈴,讓整個鄉村變得幽香而透明!
我愛故鄉,愛故鄉的一切事物!
槐花是故鄉的花朵,在故鄉的枝頭,它的美不容置疑。它是我的最愛,是我少年時期一飽口福的美味!
在故鄉,槐花還是最優秀的通信員。當它盛開的時候,葳蕤的夏天就要來了。我喜歡夏天,可以在雨中肆無忌憚地奔跑或者欣賞一朵朵在雨中搖曳的姿態。我一直認為自己是雨的兒子,雨水在我身上的擊打仿佛親吻的感覺!
我還是個愛懷鄉的人,對故鄉的依戀讓我的皮膚滿是故鄉的情結。每當槐花開放的日子到來,身體的某些部位就會變得癢癢,以至整個季節都無法得到安寧,舉手投足間,都帶著樹的影子……
其實,所有的故鄉人都知道,槐花是一味中藥,可以吃服,有清肝瀉火的功效。只是我們在故鄉吃槐花的那些年,遠不像時下的城里人,他們只是在吃膩了山珍海味之后,為了改一改口味,嘗嘗新鮮罷了。我們遠沒有那么矯情,也沒有那么驕奢,很多時候只是為了嗅一嗅槐花上那些故鄉的氣息。只是,這些年越來越少有槐花可以吃到了,越來越少的還有很多土生土長的植物!
我不知道在最后的故鄉,還會有多少事物要從那片土地上消失,像那些泥土式的建筑,那些曾經新鮮的野菜,在經濟效益的前提下,我不知道最后取代它們的會是什么,只知道曾經屬于鄉村的詩意正在一點點地離開……
五月,又到了槐花飄香的季節,在紛紜的陌路中,我還能順著那一路的花香回到故里嗎?
桂花
桂花:常綠灌木或小喬木。葉片橢圓形或長橢圓狀披針形;花芳香,簇生于葉腋,白色或黃色;核果長橢圓形,樹皮灰白色。性味甘、辛,溫。化痰止咳、散瘀止痛。治寒痰雍滯之咳嗽氣喘、胸滿脅痛、痰飲喘咳等;瘀滯疼痛、疝氣、牙痛、腸風血痢、口臭等。
故鄉沒有桂樹,自然沒有桂花,但我的記憶里有桂花。
其實,我記憶里的桂花只是我表姐的名字。在故鄉,以花為名是大多家長隨手拈來的事。那時候沒有誰提倡名字的個性,也不知道隨口而出的名字就將成為其一生的代號。在故鄉,很多人老了就不再有名字,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某某的爺爺或某某的奶奶,既然連名字都不用了,還起得那么奢侈干什么呢!
我們男孩的名字不是二狗就是三蛋,遠沒有女孩們來得好聽。在鄉村,沒人把名字當回事,誰都知道野生的東西生命力強,從沒想過與將來的命運牽扯。以前常聽說農村封建,可是農人的封建不過是為自己或下一代的生命謀個健康罷了!
桂花表姐遠沒有她的名字好看,胖乎乎的圓臉上,唯兩個小酒窩顯得甜潤。像我現在所能記起的也就是她的酒窩。
桂花表姐是表叔的小女兒,脾氣特別好,她總是特別疼表叔。表叔是在朝鮮戰場上受過傷的軍人,是傘兵,他一生最驕傲的事,莫過于戰友們一起接受總理的檢閱。表叔的傷忌冬天,一到冬天就犯,他曾說過,冬天會讓他說不定什么時候就去見馬克思老人家了。表叔說的時候常常是帶著笑,桂花表姐卻總是滿眼淚花。每次只要桂花表姐流淚,表叔的病情就好了很多,咳喘也顯得輕了。我一直很奇怪,難道表姐的淚水可以讓表叔的病情減輕?!
我對桂花表姐并沒有多少可以寫的往事,只是因為表叔才對她記憶深刻。我十八歲離開故鄉,回來后便留在城市。表叔七十多歲去世,只記得村里人說過,表叔能活這么久應該是一種奇跡。可是我不這么認為,表叔的生命應該和桂花表姐的愛有關,因為我知道,桂花表姐在結婚離開村子后,仍然像在家時那樣照顧著我的表叔。
現在,我已經不止一次看過桂花,還知道它“性味甘、辛,溫。有化痰止咳、散瘀止痛功效。”我相信,在表叔為表姐起名桂花的時候,他永遠不會想到這些,但這是冥冥中就已注定了一切的世界,像愛,是遺傳,更是承接!
泡桐花
泡桐花:玄參科植物泡桐的花。葉對生,寬卵形至卵形;花萼鐘形,花冠漏斗狀鐘形,紫色或淡紫色。蒴果卵圓形,頂端尖如喙,外果皮硬革質。春季開花時采收,干燥。性寒,味微苦。清熱解毒。主治:支氣管炎、急性扁桃體炎、菌痢、急性腸炎、急性結膜炎、腮腺炎、癤腫。
我一直認為泡桐花是故鄉最美麗、最巨大的花朵,像倒懸的燈盞,像一種召喚,在鄉村的最高處燃燒!
我喜歡淡紫色的泡桐花,一副平靜且不爭艷的樣子,沉默、恬靜,像故鄉的女子,溫婉且略顯羞澀!
泡桐花的香淡淡的,若有若無,我喜歡這種氣息。不知道從何時開始,我對濃郁的香味過敏,常禁不住地打噴嚏。這種結果直接導致了我對身上噴滿異香女人的厭惡,我曾說過,我是在花朵中長大,緣何會這樣,卻不清楚。
以前的故鄉,泡桐很多,花也多,現在很少了,但故鄉很多東西卻依舊沒有改變,像曾經要給我做泡桐花枕頭的女孩!
女孩是鄰家的女兒,愛收集泡桐花兒,曬干后放在一個塑料袋子里。她的身上就有那種淡淡的香味,有些像泡桐花的味道,聞著極舒服。為此,我常常找理由和她在一起,當我告訴她我喜歡她身上的味道時,她的臉漲紅了,說等她把泡桐花收集夠了,就給我縫個枕頭。我不知道泡桐花枕頭是什么樣子,但是想著她身上的味道,我興奮極了。
我最終沒能擁有泡桐花枕頭,在女孩說了要給我縫枕頭的夏天,我們搬家了。一晃十多年,我以為再不會見面,沒想到竟會在書店里相遇。當時我沒能認出她,但是她的名字和嘴角下的痣卻絲毫未變!她依舊那么清純、善良、溫柔且略略含羞。她是為可愛的小女兒買書的,她說,她們現在城里打工,在城市里生活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她還是想回鄉下,她說。說話的時候,小女兒就牽著她的衣襟盯著我看。我蹲下身,想拉過那個像她樣美麗、可愛的小女孩,沒想到她竟扭著身子不讓我牽,而她的身上竟也有種淡淡的香味,像當年的她,像泡桐花的氣息……
故鄉的女孩范文第3篇
曾經有這么一個故事。
一位身患白血病的女孩,死神之手正向她一步又一步地靠近。它,想對她伸出那尖銳的魔爪。
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
她,一天天地虛弱下去。
終于有一天,醫生知道了她在世的日子已經不久。他問她:“你有什么愿望嗎?”
女孩當然也明白自己的生命已經快到盡頭了。她的愿望,是這樣樸實:“我想去天安門廣場看一次升旗儀式。”
對于一個生命垂危的女孩的要求,我想不會有人狠心地拒絕她。可是,女孩的家在烏魯木齊,而天安門在北京,路途實在是太遙遠了!醫生怕女孩的身子承受不住旅途的勞累,在中途就……可是,又有誰狠得下心拒絕一個女孩臨終前的要求呢?
于是,在烏魯木齊,由一個兩千多人組織的隊伍,開始了升旗儀式。當國歌響起時,女孩舉起了她那一雙瘦弱的小手,向國旗敬禮……在場,許多人紛紛落下了眼淚。
故鄉的女孩范文第4篇
從此,我是一個有故鄉的人――路橋十里長街,一條內心隱秘的河流,那些閃亮的少年時光,仿佛魚群在水中自由穿行,一次次游過我的夢境。
我的名字
1980年9月15日,當我來到這個世上時,母親腦海中久久回蕩著一個名字――“相依”。當時,我的父親還在遙遠的大興安嶺,在一個叫塔河的筑路隊正度過他知青生涯的第十個年頭。當我降臨后,母親覺得我們母子倆要“相依”為命了,好在這年冬天父親如愿“返城”,一家三口,終于團聚。
不再“相依”,那取什么名字好呢?最終,父親把這個命名權交給了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祖父行使。祖父冥思苦想很多天,最后給我取了一個很像筆名的真名――“方石英”,他是冀望我能學習古人剛柔相濟的品性。長大后,我是個溫和且堅硬的人,也許這正是受了自己名字的潛移默化。而選擇寫作的道路后,我同樣希望自己的詩是質樸的、堅定的,并且是感人的,像一塊宿命的石頭,呈現作為個體的人在時代與命運的迷局里所應該持存的生命的尊嚴。
1982年的蘋果
“在晚風中,太陽是只熟透的蘋果”。那年,我剛好3歲,母親帶我去照相館拍照。
我站在一個漂亮的花壇里。拍照的伯伯看上去很和藹,他讓我站好,我就站得筆直,他讓我笑一笑,我就毫不猶豫笑得燦爛無比,他一邊騰出一只手一邊說:“好,就這么笑,往我這里看,我喊一二三。”
“一――二――”,接下來應該是鏡頭一閃“咔嚓”一聲,可是那個拍照的伯伯卻停住了。原來我的眼睛根本沒看鏡頭,而是緊緊盯著旁邊的一個小女孩,盯著她手里的一個紅蘋果。
母親看在眼里,于是走過去和小女孩的母親交涉,意思好像是借一下蘋果,讓我拿一下,拍完照就還給她們。后來那個小女孩似乎很不情愿地把蘋果遞給我,我才不管,一把抓過蘋果,兩手捧得牢牢的,那種感覺讓我舒服。
依然站得筆直,依然笑得天真燦爛,只是手上多了一個充當道具的蘋果,這回我是雙目異常有神地盯著那鏡頭,我想那時小女孩一定是緊盯著我,盯著我手里屬于她的蘋果。拍照的伯伯依然告訴我他喊“一二三”,我胸有成竹點了點頭。
“一――二――”,接下來果然聽到“咔嚓”一聲,只是閃光燈沒閃……突然那個小女孩“哇”的一聲哭了。天哪,那“咔嚓”一聲居然是我狠狠地咬了一口那不屬于我的蘋果。
母親連忙上前對那個小女孩說:“不哭,阿姨待會兒賠你一個比這個更大更紅的。”又對小女孩的母親報以一臉的尷尬,反而是那女人安慰了我母親一番。
照片最終還是拍了,依然站得筆直,依然拿著蘋果,只是我再也笑不出來,而那個蘋果的缺口正對著我的胸口。我人生中的第一張照片,就這樣定格了。
回到家母親沒有批評我什么,反而破天荒地買了一堆又大又紅的蘋果讓我吃。我居然真的吃開了,并且高興地邀請母親一起吃,母親笑著說:“你吃吧,大人不喜歡吃蘋果。”于是我信了,沒有再說什么,只是顧自己吃……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一天,母親哭了。
說書人
印象中,自我懂事起,就經常去書場聽說書。當時我們路橋文化站在老街東岳廟對面(我家也在附近),那時侯電視機還是稀罕之物,文化站為了豐富群眾文化娛樂,開辟了兩大經典項目――錄像廳與書場。
去看錄像是當時鎮上小青年的時髦事,記得當時的“楚留香”特別火爆。那時我還小,幾乎沒有零花錢,于是就去混書場。一是自己真的喜歡,二是可以免費,偶爾還能弄點小零食解饞。說書的人,我再熟悉不過,他是我的大舅父――臺州平話第一人、曲藝家蔡嘯先生。
除了在正式的書場可以聽舅舅說書,更多時候我是在自己家里的飯桌上聽舅舅講故事。那時候,蔡嘯舅舅在文化站工作,上下班都會經過我家,有時候是父母把他拉進來,有時候是他自己走進來,反正來我家吃飯喝酒的頻率是非常高的,以至舅舅也常常用老話自我調侃――“娘舅,娘舅,走來走去空雙手。”
舅舅在我家喝酒,常常演變成一對一講學,內容斑斕龐雜,繽紛多彩,對我來說就像一個萬花筒。尤其是舅舅講述他家潞河蔡氏與我家石曲方氏的各自家族往事,更是讓我久久地回味嘆息。
后記
在故鄉隱秘的河流里,我喚出“名字”“蘋果”“說書人”這三尾小魚與大家見面,其實已經泄露我最大的秘密――對我而言,寫詩也是一種回憶的過程。而有時候,更像在做夢。
作家小檔案
方石英 1980年出生于臺州路橋十里長街。“80后”代表詩人之一,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入選“首批浙江省青年作家人才庫”。著有詩集《獨自搖滾》《石頭詩》等,獲“浙江省青年文學之星優秀青年作品獎”“2009―2011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及“新荷計劃?實力作家”等獎項。現居杭州。
故鄉的女孩范文第5篇
具體地說,我的故鄉在吉林省洮南市,他雖然是個不起眼的小城,沒有山,沒有水,可我依然對這片土地充滿著無限的熱愛。因為他是我生于斯,長于斯的地方,是我牙牙學語的地方。我在這里成長了五千多個日日夜夜,在每一秒鐘,都滲透著我熾痛的熱情。
故鄉的土地是肥沃的,聽前輩們說,北大荒以前是一個富饒、很有知名度的地帶,所有的人都愿奔往這里來,而我就是那幸福的一個。每當我遙望故鄉的土地時,我想起那萬古長青的松柏,煙雨似的柳條在路旁英姿颯爽;我想起紅布似的高粱,金黃的豆粒,黑玉的眼睛,帶著松香氣味的煤塊,帶著萬里沙塵的狂風迎面襲來……
故鄉,有時就像一個健壯的青年,豪情萬丈;可她有時又像一位如花的少女,柔情激蕩。
故鄉的天,那樣親切,那樣可愛。盡管我的腳步涉足過很多地方,但當我仰望那里的天空,雖然他也很美、很藍、很高、很廣,可我卻總也找不到故鄉的那份親切之感。
故鄉的云軟綿綿的,盡管我沒有真正的觸摸過他,可我的心早已與故鄉取得了永遠的溝通,我可以感覺到,在我憂傷時,它可以溫柔的撫摸我的心,讓我把煩惱拋開,在我快樂時,她又悄悄降臨到我的心上,與我分享無盡的喜悅。我永遠也不能忘記她,因為是她給予了我無限的關懷,為我帶來了新鮮的期待。
故鄉的雨,有如針那樣細,有如光那樣亮,每一滴都深深浸透到我的心里,讓我的心不再孤獨,讓我的心感受到清新的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