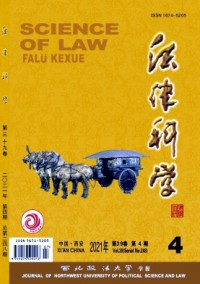法律援助論文范文精選
前言:在撰寫法律援助論文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他人的優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秀范文,希望能夠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法律援助論文:法律援助變革試點探究
本文作者:左衛民馬靜華作者單位:四川大學
試點發現之一:辯護率顯著提升
試點發現,從被告人角度,選擇免費辯護的愿意較高。在這種態度的支配下,接受了免費辯護停息告知的被告人中,選擇免費辯護的比例較大,由此使D縣法院在試點后辯護率顯著提升。受各種因素限制,①協調組沒能將免費辯護信息告知試點期間起訴到法院的所有被告人。在150名被告人中,除14人屬于指定辯護的情形,有68人接受了告知,其中,有35人選擇免費辯護,其他33人中選擇委托律師辯護的20人,選擇自我辯護的13人。隨著訴訟的進行,接受告知的被告人中,有一名先期準備委托辯護的被告人最終放棄了律師辯護,轉而進行自我辯護。故68人中的實際辯護構成為:35名免費辯護,19名委托辯護,14名自我辯護。如果考慮指定辯護也是影響辯護率的重要因素,那么,當免費辯護的權利告知程序實施之后,辯護率狀況為免費辯護為42%,委托辯護24%,指定辯護17%,自我辯護17%。這與試點前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在2007~2008年,D縣法院審理的686名被告人中,自我辯護率高達77%,而律師辯護率僅為22%,公民辯護1%。兩相比較,試點期間樣本案件的律師辯護率上升了約60%。顯然,影響辯護率變化的根本因素是增加了試點期間的免費辯護這一變量。辯護率發生顯著變化的內在原因是什么?顯然,對于選擇免費辯護的被告人來說,“有辯護必要”是其選擇律師辯護的根本原因,但在此之前他們的家人并沒有為其委托律師。這是否意味著他們的家人認為沒有必要聘請律師?考察發現,實際的情況并非如此。大部分被告人的家人都認為有請律師辯護的必要,而之所以沒有委托律師主要原因為經濟困難或者不了解聘請律師的渠道。對于“作為親屬,你認為給被告人請律師是否是必要的?”一問,17名受訪者中,認為“很有必要”和“有必要”的共有15人,占絕大多數,沒有必要的2人,說不清楚的沒有。而對于“如果你認為給被告人請律師是必要的,為什么沒有自己花錢請律師?”的追問,如表3所示,分別有接近一半的親屬選擇“請不起律師”和“不知道怎樣請律師”。盡管如此,一定比例的被告人并未認為律師辯護是一種“必需品”。接近50%的被告人仍選擇委托辯護和自我辯護,而放棄幾乎沒有任何成本的免費辯護。這與課題組在試點之前的預設大為不同。②何以如此?進一步的調查發現:一方面,對于委托律師辯護的情形來說,委托辯護律師已經確定、免費律師辯護信息告知太晚是主要原因。對19名選擇委托辯護的被告人,課題組當場進行了問卷調查,問題為“為什么委托收費律師進行辯護,而不選擇其他(免費辯護、自我辯護)的理由?”其中13人接受了調查,另6人拒絕回答,根據回答情況統計為表4。如表3所示,13名被告人之所以委托律師辯護而放棄免費辯護,家人已花錢請律師為主要的客觀原因(11人),而極少有被告人(2人)從辯護效果預期的主觀角度進行解釋。這意味著,是否委托律師其實并非取決于被告人的意愿,而是取決于家屬的安排。這是因為,所有這些被告人都被先行羈押,雖然他們失去了尋找律師、委托律師的能力,但其親屬可為其代行使權利。另一方面,就選擇自我辯護的情形而言,被告人認為事實清楚、案情較輕而無辯護必要則是其關鍵性影響因素。如表5所示,對于“如果你選擇自己辯護,不請人辯護,理由是什么?”14名選擇自我辯護的被告人中,共有10人認為“自己的案情很清楚,沒有必要請律師”(6人)或“自己案情不嚴重,沒有必要請律師”(4人),占約70%;其次是“請不請律師效果差不多”(3人);認為“案情不嚴重,自己辯護效果更好”的只有1人。
試點發現之二:辯護效果平穩
就辯護效果而言,無論是客觀性評估還是主觀性評價,試點案件中的援助辯護都有一定效果,但相比對照組案件并無突出之處。具體表現在,一方面,辯護意見采納率較高,另一方面,從司法人員角度,援助辯護與委托辯護效果大體相當。總體上,援助辯護效果可以稱之平穩。
(一)辯護意見的采納情況
大學法律援助發展思考論文
摘要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不斷發展,法制建設得到了不斷的完善,并取得了顯著成效。由于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存在著大面積的弱勢群體,特別是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法盲依然存在。為了更好地促進我國法制文明建設,特別要在高校法制文明建設的進程中,大學生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對于大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能讓他們打得起官司,能平等地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重大意義。本文將結合筆者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來探究大學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意義。
關鍵詞: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弱勢群體
“國無法不立”,法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就像鐵軌對于火車一樣,脫離了這條軌,必將導致國家的混亂甚至國家的存亡。法律對于國家是如此之重要。我國的法制建設雖已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國所處的特殊歷史階段,我國公民在法律知識方面仍然很欠缺。特別是位于西部邊陲的人們。因此,加強法制建設,大力宣傳法律知識,不僅是國家的事,更是我們每個法學專業者的責任。同時,法學專業的學生大力普法宣傳,還是鍛煉自己的一個好機會。本著“學法用法,服務社會”的宗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了。
一、法律援助的產生
據相關材料調查顯示,我國最早出現的從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組織是武漢大學的“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它是一家民間的法律援助組織。由此可見,法律援助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近幾年才產生的,還是個新生兒。2003年7月16日國務院第15次常務會議通過并于2003年9月1日頒布施行《法律援助條例》后,我國法律援助事業進入了嶄新的階段,進入了法律化的階段。那么怎樣來給法律援助定義呢?
公民保護法律援助探討論文
一、法律援助的立法意義和目的
法律援助是對那些需要參與訴訟或者需要與有關國家機關交涉事項,但經濟上又非常困難,請不起人、辯護人的公民,由國家為其提供免費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公民,特別是困難的公民獲得法律援助,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一項公民權利。自20世紀中葉以來,已有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相繼建立起了與本國實際相適應的法律援助制度,開展了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活動,使那些需要法律援助但經濟上又困難的公民,能夠獲得由國家為其提供減、免費用的法律服務。我國的法律援助工作自1994年開始在部分省、市進行試點,1996年起在全國各地逐步推開,對維護司法公正、調解和處理社會矛盾,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市是從2001年起步的。2003年7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385號公布了《法律援助條例》,條例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其立法的意義和目的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1、保障公民獲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保障公民獲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是實現“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一憲法原則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條例立法的根本目的。公民有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從而公民有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保障公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是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直接目標,即保障公民不因經濟困難而失去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
2、促進和規范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其具體的實施工作亦需要法律、法規的規范和保障,這已是當今世界已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實踐以及我國法律援助立法前后的法律援助工作實踐所證明了的,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公民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并平等地實現公民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對于法律援助的對象和范圍、法律援助的申請與審查、法律援助的實施與程序、法律援助的管理體制以及法律責任等一系列可操作性規范,都需要以制度化的形式予以規范,從而保證公民平等地獲得應有的法律援助,也使法律援助機構和法律援助人員的活動按照一定的規范運作。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律援助條例》立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使法律援助制度的運作實施達到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以確保法律援助制度的社會功能得到真實、有效的實現。
二、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和應具備的條件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法律援助是一項政府主辦的事業,立法中確定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是,既要借鑒國際上的通行做法,又要考慮我國國情;既要考慮所涉及的案件情況,又要考慮當事人經濟困難的程度;既要考慮能讓經濟困難的公民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又要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適用范圍包括兩個方面:
法律援助立法探討論文
一、法律援助的立法意義和目的
法律援助是對那些需要參與訴訟或者需要與有關國家機關交涉事項,但經濟上又非常困難,請不起人、辯護人的公民,由國家為其提供免費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公民,特別是困難的公民獲得法律援助,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一項公民權利。自20世紀中葉以來,已有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相繼建立起了與本國實際相適應的法律援助制度,開展了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活動,使那些需要法律援助但經濟上又困難的公民,能夠獲得由國家為其提供減、免費用的法律服務。我國的法律援助工作自1994年開始在部分省、市進行試點,1996年起在全國各地逐步推開,對維護司法公正、調解和處理社會矛盾,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市是從2001年起步的。2003年7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385號公布了《法律援助條例》,條例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其立法的意義和目的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1、保障公民獲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保障公民獲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是實現“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一憲法原則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條例立法的根本目的。公民有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從而公民有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保障公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是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直接目標,即保障公民不因經濟困難而失去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
2、促進和規范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其具體的實施工作亦需要法律、法規的規范和保障,這已是當今世界已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實踐以及我國法律援助立法前后的法律援助工作實踐所證明了的,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公民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并平等地實現公民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對于法律援助的對象和范圍、法律援助的申請與審查、法律援助的實施與程序、法律援助的管理體制以及法律責任等一系列可操作性規范,都需要以制度化的形式予以規范,從而保證公民平等地獲得應有的法律援助,也使法律援助機構和法律援助人員的活動按照一定的規范運作。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律援助條例》立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使法律援助制度的運作實施達到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以確保法律援助制度的社會功能得到真實、有效的實現。
二、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和應具備的條件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法律援助是一項政府主辦的事業,立法中確定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是,既要借鑒國際上的通行做法,又要考慮我國國情;既要考慮所涉及的案件情況,又要考慮當事人經濟困難的程度;既要考慮能讓經濟困難的公民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又要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適用范圍包括兩個方面:
刑事法律援助制完善論文
由于種種原因,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請法律援助的困難群體中,每年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這項制度。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工作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與發達國家已成熟的制度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質保障能力與工作發展需要有距離,法律援助服務能力與困難群眾法律援助需求有距離。
一、我國現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認識不夠,沒有認識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較晚,社會對其的認識也較模糊,還有不少人認為這只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慈善行為,只是國家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給予經濟困難者的幫助。某些地方甚至將刑事法律援助的職責都推給社會律師,變成全部是由社會律師承擔的義務,沒有將刑事法律援助作為人權來保障,沒有認識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沒有認識到這是政府的職責。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僅是由于當事人經濟困難,更在于案件性質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刑事訴訟機制中,犯罪嫌疑人與刑事被告人處于當然的弱勢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訴訟事關犯罪嫌疑人與刑事被告人的財產權、自由權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權利。因此,對其在訴訟中的權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辯護律師,更應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窄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34條及《條例》的規定,我國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適用于兩類人群,一類以經濟困難為前提條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訴案件中的自訴人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訴訟人的。另一類是不以經濟困難為前提條件,但僅限于被告人是盲、聾、啞或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從此規定來看,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除了自訴案件的被訴人外都覆蓋了,范圍不可謂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只規定了指定辯護,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間只限于公訴人出庭公訴階段,基于上位法與下位法的關系,《條例》對公檢法并沒有強約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蓋面相當窄。另一方面從實際操作來看,“對于《條例》第11條所規定的三類案件,當事人申請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沒有為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從經濟審查標準分析,對非指定辯護的受援人的經濟困難審查是較為苛刻的,一般規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線之上的20%左右,這就極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圍。如云南省2005年全省辦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過申請的352件,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為法院指定案件。2005年,全國各地的法律援助機構辦理法律援助案件25萬多件,接待法律咨詢200多萬人次,有43萬多名困難群眾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長48%。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請法律援助的困難群體中,每年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這項制度。